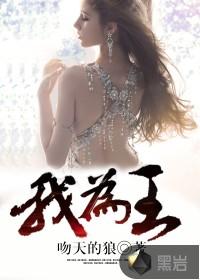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小卡比兽叶银川无防盗章节列表 > 第535章 真正的天空霸主传说宝可梦烈空坐令人绝望的破坏光线(第2页)
第535章 真正的天空霸主传说宝可梦烈空坐令人绝望的破坏光线(第2页)
阿禾点头,调低增益,将麦克风轻轻递过去。
老人坐了下来,双手紧握拐杖,指节泛白。
“我叫李志邦,19年参军,参加过抗美援朝。”
他开口时声音沙哑,像是从井底捞上来的铁链摩擦着石壁,“1952年冬天,我们在长津湖边上守一个高地。
零下四十度,很多人脚趾冻黑了,剪掉也不喊疼。
但我们最怕的不是冷,是寂静。”
他闭了闭眼。
“那天晚上,敌军炮击停了。
整个战场突然安静下来,静得能听见雪落在钢盔上的声音。
有个四川兵,才十七岁,忽然开始唱歌。
唱的是《康定情歌》。
他声音不大,但我们都听见了。
接着,左边来了个山西的,哼起了梆子;右边是个上海人,吹口哨学评弹。
最后,整条战壕的人都在唱,有的跑调,有的哭着唱,可没人阻止。”
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清点人数,活下来的不到三分之一。
可你知道最奇怪的是什么吗?战后档案里,根本没有这场‘集体歌唱’的记录。
上级说:‘不可能,战场上哪有人敢擅自发声?影响纪律!
’”
老人苦笑一声。
“可我记得。
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我都记得。
因为那是我们唯一一次,不是作为战士,而是作为‘人’,一起活过的证明。”
他说完,久久不语。
阿禾没有打断,任磁带静静转动。
直到老人自己睁开眼,轻声说:“谢谢你让我再说一遍。”
她收起设备,认真写下标签:
**第九个故事?第一段:长津湖的夜歌**
临走前,老人忽然拉住她的手腕:“丫头,你们这玩意儿……真能把声音送到天上吗?”
阿禾望着天空飘过的云,想起林小满说过的话。
“不是送到天上。”
她说,“是送回心里。
只要还有人愿意听,那些声音就不会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