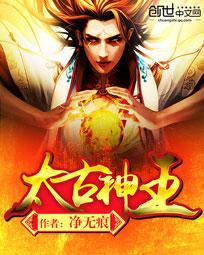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重生从1993开始 > 第一三五三章 大象和蚂蚁(第1页)
第一三五三章 大象和蚂蚁(第1页)
对着电话,又喂了几声,却都没有再听到动静,让胡明义不由一阵古怪,不知道卢建章这是怎么了。
不过,胡明义也并没有将这件事太放在心上,只以为,是安电公司那边,走关系,走到了卢家那边罢了。
话说。。。
夜风穿窗,拂动书桌上的纸页,那句“我在听”在录音笔中循环了三遍,才渐渐淡去。唐俊站在院门口,望着远处山脊被月光勾勒出的轮廓,仿佛看见无数条无形的声波正从大地深处升起,如藤蔓般缠绕着空气,向天空攀爬。他没有回头,却知道那支录音笔仍在工作??它已不再只是记录工具,而是一扇门,一扇通往所有沉默灵魂的窄门。
他缓缓坐下,从怀中取出母亲留下的那枚铜铃。铃身早已失去光泽,边缘布满细密划痕,像是被岁月啃噬过无数次。这是她唯一留给他的信物,据父亲说,是她在逃亡途中从一位老尼姑手中换来的护身符。如今握在手里,竟微微发烫,如同回应某种召唤。
“你听见了吗?”一个声音忽然响起。
唐俊一惊,转头望去,阿?不知何时已站在院中,赤脚踩在青石板上,脸上依旧带着那种近乎通透的平静。她的眼睛虽看不见,却像能穿透时空。
“什么?”他低声问。
“土地在说话。”她说,“不是用耳朵听的那种话。是心和骨头一起震出来的声音。刚才……有个男人哭了,就在你身后那棵树下。”
唐俊猛地回头。那里只有一棵百年樟树,树皮皲裂如老人手掌,枝干扭曲向上,像在挣扎着够什么。可此刻,树影斑驳间,似乎真有水珠从空中坠落,砸在石板上,发出极轻的一响。
他起身走近,伸手触碰树干。指尖刚触及粗糙表皮,一股冰凉的颤栗便顺着手臂直冲脑髓。眼前骤然浮现画面:一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跪在树下,双手抱着一封信,额头抵着树根,肩膀剧烈抖动。信纸泛黄,字迹模糊,但依稀可辨:
>“阿妹:
>我不能回来娶你了。战事紧急,部队连夜转移。若我不幸阵亡,请替我看看春天的山花。你说过,最喜欢杜鹃开时的样子……”
画面戛然而止。
唐俊踉跄后退一步,呼吸急促。这不是记忆,也不是幻觉??这是**现场回放**。那封信从未寄出,埋在树洞里几十年,直到今夜,才随着树根吸收的地脉共振,将主人的情感释放出来。
“他是谁?”阿?轻声问。
“我不知道。”唐俊嗓音沙哑,“但我能感觉到……他死得很早,还没来得及活成自己想成为的人。”
阿?点点头,蹲下身,手指轻轻抚过地面。“这里还有很多。”她说,“他们不敢大声哭,怕惊扰活着的人;不敢写名字,怕连累家人。可现在不一样了。风愿意带话,石头愿意记事,连雨水都学会了传情。”
唐俊怔住。
他忽然明白,“共忆网络”之所以能在1993年启动,正是因为那一年,世界正处于巨大断裂之中:冷战结束、旧秩序崩塌、千万人流离失所。那些来不及说出口的话、未能完成的告别、被时代碾碎的爱情与信仰,全都沉入地底,等待一个频率来唤醒。而他手中的共振仪、母亲埋下的铁盒、西伯利亚晶体的分裂……不过是导火索。真正的引信,是人类集体压抑太久的**未竟之声**。
第二天清晨,怒江边传来消息:那本日记的主人亲属找到了。是一位八十二岁的老太太,住在保山乡下。当村干部把复印件送到她手中时,她盯着最后一页看了足足十分钟,然后突然放声大哭。她说那是她姐姐,名叫阿?,十七岁爱上一名远征军士兵,两人私定终身,却被家族强行拆散。士兵临走前答应打完仗就回来迎娶,结果再无音讯。阿?不信他死了,每年春节都穿上红衣,在村口等一天。
“她到死都没改嫁。”老太太抽泣着说,“她说,只要她还活着,他就没真正离开。”
消息传回梧桐山时,唐俊正坐在廊下修理一台老旧收音机。听到这番话,他手一抖,焊锡滴在指尖,烫出一个小泡。他没管,只是默默调频,试图接收到某个特定波段。
“你在找什么?”阿依古丽走进院子,肩上背着新一批感知者的培训资料。
“我想试试看,能不能让阿?的声音传出去。”他说,“不只是给她妹妹听,而是让所有还在等待的人听见??哪怕对方已经不在了,那份守候本身,也值得被铭记。”
阿依古丽沉默片刻,从包里拿出一块微型芯片:“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情感编码器’。可以把一段纯粹的情绪压缩成声波信号,通过自然介质传播。比如风、水、岩石。它不依赖电力,靠的是……共鸣。”
唐俊接过芯片,小心翼翼焊接到收音机电路中。然后,他将阿?日记的扫描件贴在喇叭外罩上,按下播放键。
起初什么也没有。只有电流的滋啦声。
接着,一阵微弱的哼唱缓缓浮现,正是那首《摆时》调的变奏,但节奏更缓,带着一种近乎透明的哀伤。歌声并不完整,断断续续,仿佛随时会被风吹散。可就在这破碎的旋律里,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力量??那是五十年孤独的重量,是一颗心如何在绝望中依然选择相信的证明。
收音机自动转向东南方向,像是被某种力量牵引。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保山山村,老太太正坐在堂屋门槛上晒太阳。忽然,院子里的老槐树无风自动,树叶沙沙作响,竟与收音机传出的旋律完全同步。她抬起头,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