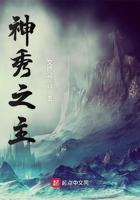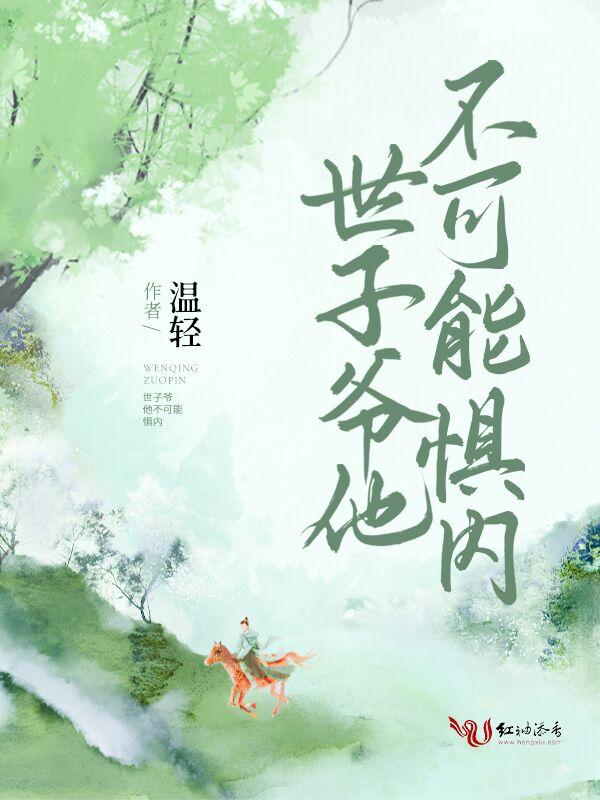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大明:哥,和尚没前途,咱造反吧 > 第一千一百六十章 藏锋宴终是来了(第2页)
第一千一百六十章 藏锋宴终是来了(第2页)
“是遵礼法乎?是守君命乎?是听百官之议乎?”
“非也。”他声音不大,却掷地有声,“正者,先正其心,次正其行,终正其道。”
众人交头接耳,议论四起。
薛明渊眼神微动,低声与旁人道:“此言。。。。。。。非少年之语。”
李洪甫须不语,只望着台上年轻的太子,眼中闪出异色。
朱标继续道:“今上勤政,百官治事,我太子无为,惟当正心明道,不辱国本,不辱皇命。”
“若我为储君,日后践位,必以明法为先、以听民为中,以尊儒为本。”
“国子监者,天下学子归心之所,今日我于此讲,不为权,不为利,只愿尔等将来入仕,不负天下之心。”
讲坛之下,寂静无声。
忽有人起身,重重一拜:“愿从太子之志。”
紧接着,众人起立,齐声:“愿从太子之志!”
声如雷动,传遍国子监内外。
远处观台上,朱瀚手执玉简而立,神色未动,手却轻轻捏紧了玉简一角。
他身旁,陈鹤鸣目露狂喜:“王爷,太子。。。。。。立威了。
“这才是第一步。”朱瀚缓缓道,“让人盯紧薛明渊。”
“是怕他反对?"
“不。”朱瀚淡淡道,“他若反对,反成了我之力。”
“那王爷是。。。。。。”
“我怕他不反。”
陈鹤鸣一怔,随即恍然:“王爷是要借他之口,将太子之道送入朝中?”
朱瀚点头:“若要百官听太子,非得先让他们信太子。”
而在皇宫深处,御书房中。
朱元璋静坐,手中却紧握一封从国子监传回的快简。
“这小子。。。。。。”他咧嘴一笑,“还真讲得一套好道理。”
他转头对身旁的中官道:“传朕旨,赐太子今日之讲为‘春坛讲德,编入太学课卷。”
“诺!”
朱元璋放下书卷,低声咕哝一句:“朱标,若你真能担得起。。。。。。这皇叔,倒也没白护你。”
翌日,太学门前便贴出告条,一纸“春坛讲德”,赫然书明太子之志。
坊间书肆也将“太子春坛讲义”摹刻成册,几日内风行四方,甚至有儒者将之与《中庸》《论语》并列,称其“可传后世,立君子之志”。
这一切落入朱瀚眼中,只一言:“起势了。”
“王爷,薛明渊已于今晨入宫,太子尚在东宫未动。”
陈鹤鸣脚步急促,面色微带肃然,“听闻是太学正李洪甫引荐,今晨朝散之后便直入文渊阁。”
朱瀚却微一挑眉,缓声笑道:“有趣,薛明渊竟不疾言以驳,而甘愿入朝,这一招,不像是他。
“王爷,您怀疑。。。。。”
“不急。”朱瀚拈起一枚棋子,落于棋盘一角,“他若只为反驳,自可于朝堂上击之,为何偏偏绕道?他是聪明人,怕是想借此抛出条件。”
“条件?”
“嗯。士林中人,总要落得实地才敢行远志。
朱瀚语罢,缓步走向窗前,望着天光洒下的金瓦朱墙,低声道:“他若要议议事,我便给他事。但这事,由我设。”
“传话下去。”
“王爷,您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