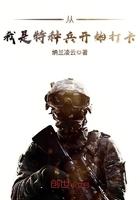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春色满棠 > 第441章 分赏酸枣仁(第1页)
第441章 分赏酸枣仁(第1页)
消息传回京,小皇帝当日上朝就很愤怒,当堂痛斥暴民狂悖,藐视朝廷。
他发完怒,另指了名忠于梁氏皇族的朝臣南下监督水利,并承诺差事办完回来,给这朝臣升官。
但同僚才被暴民给杀了,脑袋都被捶扁了,可见暴民有多凶残,去了说不定就跟同僚一样回不来了。
这位朝臣当即表示他最近腿疾发作,每日来上朝都需要家奴扶着才能上下马车,怕腿脚不利索南下会耽误了小皇帝派给他的差事。
小皇帝看了这朝臣一眼。
朝臣觉得小皇帝的眼神。。。。。。
沈砚在清明祭典后的第三日,独自一人登上了知棠学宫后山的望心崖。崖高百丈,下临深谷,云雾缭绕如练,相传是历代医者静思悟道之所。他手中仍攥着那封从树洞取出的绢书,字迹清瘦却有力,笔锋间似有风雪穿行之感。他一字一句反复读着:“岭南近日多雨,寒湿侵体,慎防‘阴疽流毒’。”
可岭南此刻晴暖无雨,村中井水清冽,连老郎中都说今年春气和顺,疫病难起。
他不解。
更令他心头微颤的是落款??“知棠”。不是“知棠学宫”,也不是“守档司传讯”,而是她亲笔所署。仿佛那一夜星光裂云,并非幻象,而是她真正在人间留下的一缕呼吸。
他在崖边盘膝而坐,闭目调息。三年来,他已学会以脉察情、以声辨症,甚至能从病人咳嗽的节奏里听出其家中灶火是否常熄。但这一次,他听不出这封信的来处。它不像预警,倒像一声轻唤,自遥远之地拨动心弦。
忽然,风中传来一阵极细的脚步声。
不像是人走,更像是……赤足踏过青苔。
他睁眼,只见崖口雾中走出一道白衣身影。身形纤slender,发间玉簪微光闪烁,与照心镜中所见一般无二。她并未靠近,只立于三步之外,目光沉静如古井映月。
“你来了。”她说。
沈砚竟不觉起身,喉头一紧,竟说不出话。他想跪,又不敢;想问,又怕惊扰了这场梦。良久,才低声道:“您……真是知棠先生?”
女子轻轻摇头:“我不是你要找的那个‘先生’。我只是她的影子,藏在这片山雾里的记忆之一。每当有人真心追寻医道本源,我们便会被唤醒。”
“那……祖母呢?”沈砚脱口而出。
女子眸光微动:“你说孟婉清的女儿?她确曾来过此地,三十年前。那时她身染奇疾,高烧七日不退,口中喃喃‘井边的梅树该剪枝了’……和你母亲一模一样。”
沈砚浑身一震。
“她们得的是同一种病,叫‘心语热’。”女子缓缓道,“不是风寒暑湿所致,而是积郁成疾??话堵在心里太久,终化为火毒攻心。唯有听见她们真正想说的,才能解。”
“可我母亲……她明明没有梅树!”
“但她心里有。”女子望着他,“你母亲小时候,村里曾有一株老梅,每年开时,她都去捡花瓣晒干泡茶。后来战乱毁园,梅树被砍,她再未提起。可那份遗憾,一直埋着。等到临终之际,意识涣散,潜藏心底几十年的痛,终于浮上来,变成了遗言。”
沈砚双膝一软,几乎跌坐。
原来母亲不是神志不清,而是在用最后力气,告诉他:**我也有舍不得的东西,就像你舍不得我一样。**
“所以……”他声音颤抖,“治病的关键,从来不是药?”
“是回应。”女子答,“当一个人说出‘井边的梅树该剪枝了’,她在求的不是剪刀,而是有人懂她这一生有多少事来不及做完。你母亲写下‘嫁妆钱留给你’,是怕你觉得她抛下你;而她说那句看似无关的话,是希望你能记得,她也曾是个爱花的女孩。”
沈砚低头,泪水砸进泥土。
“那你为何现在出现?”他抬头,“还有那封信……若非警示,又是为何?”
女子抬手,指向南方天际:“你看那边。”
沈砚顺她所指望去,只见远处云端隐约泛着灰紫色的光晕,如同瘴气凝聚,却又带着金属般的冷意。那不是自然形成的雾,而是某种人为炼制的气息。
“那是‘阴疽流毒’的前兆。”她说,“并非来自天气,而是有人在暗中施术,将百万人的情绪怨念炼成疫毒,欲借春气升发之时,引动天下大疫。”
“谁会这么做?”
“忘了痛苦的人。”她声音渐冷,“他们以为苦难可以抹除,于是把灾祸封存于地下、海底、深山。可苦不会消失,只会沉淀、发酵,终成毒瘤。如今,那些被遗忘的哀嚎,要回来了。”
沈砚猛然想起《疾苦录》中一段记载:古有邪医,采万人悲声炼“怨髓”,以控生死,称“逆命之道”。后被知棠封印于南海断渊之下。
“难道……封印松动了?”
女子点头:“正是。而你母亲与孟婉清所患的心语热,正是第一批被唤醒的症状。她们的梦呓,其实是远古疾苦的回响,在寻找能听见的人。”
沈砚怔住。
难怪两代人病症相同,言语相似??她们不是偶然发病,而是血脉深处的记忆被触动了。
“所以您让我带红土种下血语棠,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