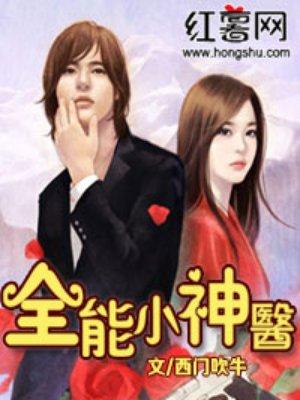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金殿销香 > 297实话(第2页)
297实话(第2页)
话音落,万籁俱寂。忽然,一阵清风穿林而过,所有灯火齐齐亮起,竟无一熄灭。更奇者,空中浮现出淡淡光影,五位女子并肩而立,衣袂飘然,正是她们年轻时的模样。孩子们惊呼跪拜,阿箬却笑了,轻声说:“你们来了。”
那一夜,千里之外的岭南山村,明心躺在竹床上,气息微弱。侍女忽惊呼:“师父!窗外有光!”
明心艰难转头,只见庭院中五盏灯凭空浮现,排列成莲花之形。她嘴角微扬,喃喃:“瞧,她们都来了……我没有输。”
她抬起枯瘦的手,指向天空,“告诉那些孩子……活下去,好好活,就是对老师最好的报答。”
言毕,含笑而逝。那一刻,岭南群山回荡一声钟鸣,虽无寺院,却响彻云霄。
三年后,听钟楼扩建为“五明书院江南分院”,招收不限性别,但特别设立“孤女助学廊”,专收战乱遗孤、弃婴、妓户之女。阿箬亲自编写教材,除医术、律法、算学外,另设“心性课”,讲授“何为良知”、“为何宽恕”、“怎样爱人而不失自我”。
一日课毕,有学生提问:“先生常说‘历史会被篡改’,那我们写的这些东西,将来也会被人烧掉吗?”
阿箬沉吟片刻,带她们走入后园。那里立着一块无字石碑,碑底埋有陶匣,内藏《金殿销香录》正本及四位姐妹口述实录。“会的,也许有一天,这块碑也会被推倒,这本书也会化为灰烬。”她抚摸石面,“但只要还有一个人记得其中一句话,哪怕只是‘该回家了’这样简单的话,我们就没真正消失。”
她转身凝视学子们的眼睛:“你们才是真正的史官。不是用笔写史,而是用一生去活出那段历史。”
十年光阴流转,阿箬年逾九旬,步履蹒跚,却仍每日清晨听钟。她的银针早已不再用于治病,而是挂在书房墙上,成为一种象征。人们传说,那针能驱邪避祸,其实只有她自己知道,它只是提醒她??那一夜发下的誓:“永不复仇,唯以仁心济世。”
某个春寒料峭的早晨,她没有出现在窗边。弟子们进房探视,发现她安卧榻上,面容平静,手中紧握铜钱,唇边带着笑意。枕边留有一纸短笺:
>我去接引下一个做梦的人。
>莫哀,莫念,莫停步。
>钟声不止,便是我在。
众人遵其遗愿,不立墓碑,不建祠堂,只将她的青帷马车停放于听钟楼下,车中置银针一支、铜钱一枚、《百草图谱》一部。每逢春至,总有陌生女孩前来叩门求学,自称“梦见白发阿婆招手”。书院照收不误,因她们带来的,往往是早已失传的药方或歌谣。
又三十年,大晟王朝覆灭,新朝建立,下令清除前朝“妖妄之说”,五明书院尽遭查封,典籍焚毁。士兵冲入听钟楼时,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唯有那辆马车静静停放,车帘微动,似有人刚刚离去。火焰吞噬梁柱之际,一道钟声自地下升起,悠远绵长,响了整整九下,而后戛然而止。
次日清晨,百姓发现废墟中央立着一根木柱,柱上刻着一行小字:“心不死,灯不灭。”
不知是谁,在柱前放了一朵干枯的梅花,花瓣边缘泛着淡淡的朱砂红。
百年之后,考古队在此地发掘出一条密道,通往地下石室。室内陈设简朴:五张木椅围一圈,桌上放着五杯茶,杯沿残留茶渍,竟未完全蒸发。墙上刻满文字,乃是历代受助女子留下的手记,最早可追溯至贞悯年间。最醒目的,是一幅炭笔画??五位女子并肩行走于山道,身后跟着无数孩童,个个手中提灯。
研究人员震惊不已:这些壁画至少存在两百年以上,但颜料成分分析显示,其中含有现代才有的稳定剂。更诡异的是,每当有人试图拍照记录,相机便会自动关机;录音设备则只能捕捉到一段模糊的女声哼唱:“梅落空山寂,钟鸣旧梦回……”
最终,政府决定封闭遗址,仅对外展出部分拓片。展览名为:“她们从未离开”。
而在遥远的北方边境,一位退休教师每年春天都会组织学生朗诵一首诗。记者问她为何坚持,她笑着说:“因为我小时候做过一个梦,梦见五个婆婆教我写字。醒来后,枕头底下压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你是续香者。’”
与此同时,在南方海岛渔村,一名女医生每逢大雨必巡视海岸,她说:“我总觉得,会有一个人乘着青帷马车而来,带着药箱和微笑,告诉我该往何处去。”
而在西域古城遗址,游客常在黄昏听见隐约钟声。导游解释:“那是风穿过断壁的声音。”但总有些孩子坚持说:“不是风,是一个老婆婆在敲钟。”
夜深人静时,国家博物馆的监控画面再次出现异常。那位白发老妪又一次来到展柜前,这次她没有擦拭玻璃,而是将一朵新鲜的梅花贴在竹简外罩上。安保人员冲进去时,大厅空荡,唯有空气中飘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药香,像是石菖蒲混合忍冬花的气息。
而在展厅感应系统重启的瞬间,录音再度响起??五种声线依次浮现,最后融合为一句低语:
“你看,又有一个孩子抬头看天了。”
“她想起该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