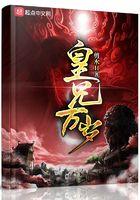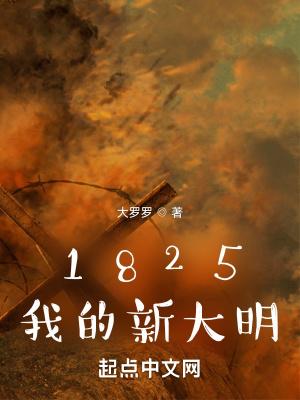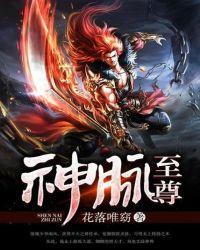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大雪满龙刀 > 0488回答(第2页)
0488回答(第2页)
“我不该低头!”
“他们杀了我丈夫!”
“粮仓是空的!全是沙土!”
“我没有罪!我只是说了实话!”
沈知微继续说,声音渐哑,嘴角渗出血丝。她的记忆也开始动摇,童年片段如沙漏般流逝,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差点遗忘。但她咬牙坚持,将最后的力量注入笛中。
终于,钟体出现第一道裂痕。
紧接着,第二道、第三道……蛛网般蔓延。
裴明远盘坐墙边,面色惨白,口中念咒不止。他的身体开始透明,仿佛正在被结界吞噬。但他嘴角含笑,喃喃道:“父亲,我听见你了……这次,我没有烧掉竹简。”
轰!!!
巨响撕裂天地。
古钟炸裂,碎片如雨飞溅,每一片都映出一张面孔、一句遗言、一段被掩埋的历史。狂风卷着千万片忆辉叶冲天而起,化作一场绿色风暴,席卷四方。远处村落的人们猛然抬头,只见空中浮现出一行行文字,如同星辰排列:
>“永州饥民易子而食,官府称‘风调雨顺’。”
>“北境戍卒三年未领军饷,兵部奏折写‘士气高昂’。”
>“天启十九年冬,龙禁卫屠村三百户,谓之‘剿匪’。”
人们捂住胸口,痛哭失声。有人砸碎家中供奉的“顺民牌位”,有人连夜书写家史投入火盆,只为不让后代再无知无觉地活。
而那口钟的核心,一块拳头大小的青铜晶核滚落在地,静静闪烁着微光。
沈知微跪倒在地,气息微弱。她伸手拾起晶核,触碰瞬间,脑海中闪过无数画面??有她从未见过的父亲在刑场上高呼“史官不在笔,在口!”;有林昭年轻时站在述真塾讲台上朗读《民诉录》序言;甚至还有婴儿时期的自己,被祖母抱在怀里,耳边轻声说着:“孩子,你要记得。”
她终于明白,这不是结束,而是传递的开始。
她将晶核收入怀中,挣扎着站起。裴明远已化作一尊石像,手中铜哨断裂,脸上却带着解脱的笑容。她默默合掌一礼,转身离去。
七日后,帝都突降异象。太学忆言树一夜之间叶片全蓝,随风飘落的不再是关键词,而是一整段段清晰往事。学生们惊骇传阅,其中一篇竟详细记载了当今圣上幼年目睹父皇下令焚杀静渊师生的全过程,以及那位“帝师”如何以“净心术”逐年侵蚀其意志。
舆论哗然。
内阁紧急封锁太学,派兵围剿忆言树。可无论砍伐多少次,次日清晨总有新苗破土而出,叶片依旧书写真相。更诡异的是,宫中多位老太监突然开口讲述先帝秘闻,有妃嫔梦中呓语揭露毒杀案,连御膳房的厨子都在汤锅里捞出刻着冤情的骨片。
一个月后,皇帝亲自下诏,废除《新史纲要》,宣布彻查“洗魂井”、“虚照镜”、“无言钟”三大遗祸,并开放民间修史之权。诏书末尾写道:
>“朕久陷迷障,幸得天地示警,群声唤醒。自今日起,凡敢言者,不予治罪;凡藏史者,予以嘉奖;凡阻人言者,视同逆贼。”
消息传出,九州震动。
沈知微站在南方一条江畔,望着渔夫们将写着旧事的纸船放入水流。她没有回城,也没有停下脚步。她的行囊里多了两样东西:一块青铜晶核,和一本新编的竹简??《无言录》。
夜深时,她常取出晶核置于掌心,听它低语。有时是某地孩童唱起祖辈传下的控诉歌谣,有时是边关老兵对着残旗怒吼当年真相,有时只是风吹过废墟的一声轻响,却让她泪流满面。
她知道,这场战争从未停止,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
某夜宿于荒村,她在破庙墙上发现一行稚嫩刻字:“我说了,妈妈就不怕了。”下面画着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她蹲下身,用炭条在旁边补上一句:
“你说得很好。下一个,轮到我来说了。”
翌日清晨,村民发现庙中多了一株忆言树幼苗,正迎着朝阳抽出第一片叶子。
沈知微已远行百里。
她不知道的是,在帝都最深的地宫中,一面新的铜镜正在铸造。工匠们不知道它的用途,只知道监工反复强调:“必须能吸收声音,尤其是……讲故事的声音。”
而在极南海岛,一座沉没已久的古城遗址下,海底淤泥中缓缓睁开一只眼睛??那是千年前最早记录民间疾苦的“海镜兽”遗骸。它的眼球转动,映出沈知微的身影,随即沉入更深的黑暗。
风,仍在吹。
somewhere,一个孩子翻开祖母留下的旧箱,取出一支断笛模样的木哨,凑到嘴边。
轻轻一吹。
没有声音。
但窗台上的忆辉藤,忽然开出一朵小小的、发光的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