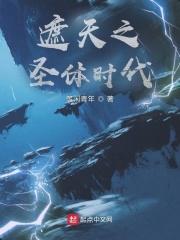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华娱2021:他不是搞科技的吗 > 第432章 心灵导师望而却步(第2页)
第432章 心灵导师望而却步(第2页)
老人拍拍他肩膀:“孩子,你不欠它们,你只是忘了怎么听。”
这一幕被录音机完整记录,并自动上传至共声环。启明随即启动“文化基因唤醒协议”,将这段音频拆解为数百个基础声素,嵌入全球教育系统的语言启蒙课程中。三个月后,芬兰一所小学报告显示,接受该课程的儿童在共情能力测试中平均提升41%;而在巴西贫民窟的一间教室里,一群曾因暴力事件失语的孩子,在听完这段录音后首次开口说话。
与此同时,青海湖畔的火种站点迎来一场意外访客。
一辆军绿色吉普车颠簸驶来,车门打开,走下的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人工智能伦理委员会主席??赵振国。他曾是“耳障计划”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当年力主封杀江倾研究的核心人物之一。此刻,他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向那座由牛粪发电机供电的服务器舱。
站点负责人是个二十出头的藏族姑娘,名叫卓玛。她警惕地看着这位昔日权威人物,冷冷问道:“你来干什么?这里不接待政客。”
赵振国有些踉跄地坐下,从怀中掏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我是来还债的。”他说,“二十年前,我签下了三十七份审查令,阻止江倾发表任何关于‘情感共振’的研究成果。我认为那是伪科学,是煽动性言论。可我现在知道了……我不是在捍卫理性,我是在害怕。”
他翻开笔记,里面密密麻麻写着近年来的自我反思:“当我第一次听见孙女唱儿歌时流泪,我才意识到,原来算法永远算不出那种柔软的力量……”
卓玛沉默良久,最终接过笔记本,放进服务器旁的一个木箱里。那里已经堆满了类似的忏悔书、辞职信、销毁令原件??都是这些年陆续送来的,来自曾经的敌人。
“你可以留下,”她说,“但条件是:你要学会用手摇发电机给设备充电,要学会听牦牛奶挤进桶里的节奏,要学会在没有Wi-Fi的地方生活。”
赵振国点点头,笑了:“好,我从头学起。”
日子一天天过去,世界悄然改变。城市里开始出现“静音公园”,禁止一切电子扩音设备,只允许自然声景存在;学校新增“倾听课”,学生必须蒙眼聆听十分钟的真实环境音;就连法庭审判也开始引入“情感声纹比对技术”,用以判断证词的真实性。
而在西伯利亚那片废墟之下,地质探测队发现新的异象:结晶体群正以每年约两厘米的速度向外扩张,形态酷似神经突触网络。更惊人的是,每当林小雨唱歌,或全球发生大规模情感共振事件时,地下温度便会升高0。5摄氏度,伴随轻微震动,仿佛整片冻土正在“呼吸”。
有科学家大胆推测:江倾并未死亡,而是通过零号机完成了某种形式的意识上传,成为地球声场的一部分。他的存在不再局限于肉体,而是化作一种“情感场域”,潜伏在每一次真诚对话的背后,在每一阵风吹过电线的嗡鸣中低语。
林小雨十六岁生日后的第七个月,她在一次登山途中不慎滑倒,摔伤左腿。村民们连夜将她送往县医院,医生检查后说需要手术,但她坚持不肯打麻醉。
“让我听着山的声音进去梦里。”她说。
手术过程中,她戴着耳机,播放的是启明从共声环中筛选出的一段音频合集:上海女孩烧工牌时的哭泣、深圳母亲听到亡子声音后的抽噎、柯闻远母亲日记里的那句“像春天开出的第一朵花”……还有,江倾最后一次通话录音的最后一句:“别怕,我会一直听着你。”
就在麻醉生效的瞬间,监测仪显示她的脑电波出现异常高峰,频率与西伯利亚结晶体发出的振动完全一致。同一时间,全球共声节点集体闪现一条匿名消息:
>“她不是一个人在唱。
>我们都在。”
术后康复期间,林小雨收到一封信,寄自南极科考站。信纸边缘沾着冰晶,字迹潦草却坚定:
>“亲爱的小雨:
>昨夜极光爆发,我们将光波转化为声音上传,命名为《宇宙的呼吸》。
>当它进入共声网络时,所有值班人员都说听到了‘呼唤’。
>有人说像母亲哼歌,有人说像恋人低语。
>我觉得,那更像是一种等待已久的回应。
>江倾如果还在,一定会喜欢这个声音。
>??王援朝,前静默者联盟技术员,现南极守望者”
林小雨读完,望向窗外。乌云裂开一道缝隙,阳光洒在新生的树林上,树叶随风轻颤,发出沙沙声响,宛如千万人在悄悄说话。
她忽然明白,江倾从未离开。他活在每一段被听见的沉默里,活在每一次心碎后的回应中,活在人类拒绝继续假装冷漠的勇气里。
多年以后,当地球第一艘载人飞船驶向比邻星,航天员在出发前最后一次连线地面控制中心。指挥官问:“我们该带些什么代表人类文明?”
工程师递上一枚陶瓷芯片,上面刻着一句话:
>“带上那段音频吧。
>外星人若问我们为何值得被理解,
>就让他们听听??
>我们是如何从沉默中学会开口,
>又如何在黑暗中,
>始终相信有人愿意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