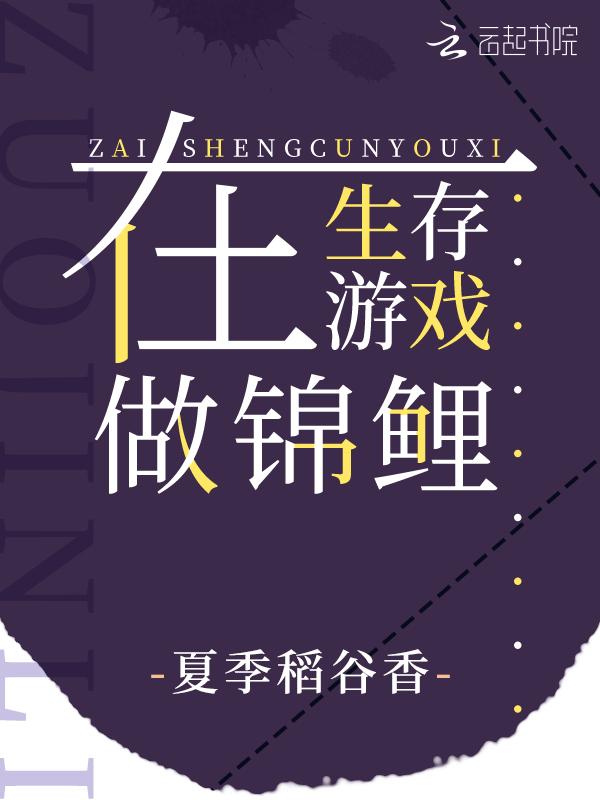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从送子鲤鱼到天庭仙官 > 第四百九十一章 借壳上市(第1页)
第四百九十一章 借壳上市(第1页)
游鸣抬头看着幽陵君,随着【重度平静】的力量被撤销,幽陵君的身上的气机再次变得狂暴起来。
那些构成他身体的无数个意识,再次充斥着负面的力量。
好不容易平复下去的黑潮,此刻再次翻涌起来。
。。。
夜色如墨,浸透了镇山的每一道石阶。月光斜洒在无字碑上,那三朵野菊依旧静静开放,花瓣微微颤动,似在回应某种遥远的召唤。湖面不再有波澜,却隐隐泛着一层银辉,像是水底藏了一轮未升的月亮。
林知悔的身影已不见于虹桥尽头,但她的声音并未消失。
它化作风,穿行于山谷之间;它凝成露,滴落在孩童梦中;它藏在医者熬药时炉火的噼啪声里,也回荡在孤寡老人临终前那一声轻叹之中。她是阵眼,是心灯,是归心阵千年不灭的守望者。而她所点燃的,不只是记忆,更是无数人内心深处悄然复苏的“愿”。
这一夜,镇山之外,万里山河皆有异象。
西北荒原,一座废弃的驿站突然亮起灯火。那本该空无一人的屋内,竟传出低低诵经之声。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僧盘坐中央,手中佛珠颗颗发烫,口中念的是早已失传的《安魂往生咒》。他双目紧闭,额头渗出血珠,仿佛正承受极大痛苦。忽然,他睁开眼,瞳孔竟是金色。
“原来……是你。”他喃喃道,“三百年前,我因贪念盗取镇山舍利,致同门死于沙暴。我逃入大漠,背负罪孽一生。可昨夜,有人在我梦中点亮一盏灯,说:‘你还活着,就还有机会赎罪。’”
话音落下,他手中佛珠轰然碎裂,化作点点金光飞向天际。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深处,一尊被黄沙掩埋已久的壁画缓缓浮现??画中僧人跪于碑前,身后站着一名白衣青年,伸手扶他起身。壁画下方,一行小字悄然显现:
**“迷途知返,亦是归路。”**
而在南方密林,一场百年难遇的瘴疫正在蔓延。村寨接连覆灭,尸骨堆积如山。幸存者躲在高崖洞穴中,以草根维生,眼看就要全数覆亡。某日黄昏,一个身影从雾中走来。那人穿着破旧道袍,脸上蒙着黑巾,只露出一双清澈如水的眼。
他不语,只是将一只陶罐放在洞口,又取出一支玉笛吹奏起来。笛声悠远,带着湿润的雨意与初春的生机。随着旋律流淌,洞外的瘴气竟开始退散,枯树抽出嫩芽,腐土下钻出灵芝般的白花。孩子们喝下陶罐中的药汤,高热渐退,呼吸平稳。
有人想问他是谁,他лишь摇头:“我不是来救你们的,我只是替一个曾经被人救过的人,还一份债。”
当夜,他在寨边立了一块木牌,上书四字:
**“愿不绝,则光不止。”**
次日清晨,人已不见,唯有一枚玉笛遗落石上,笛身刻着两个极小的名字:游鸣、苏挽晴。
这世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听见那句话。
不是通过耳朵,而是透过心。
有人在绝望跳崖前,忽然听见一声轻唤:“再试一次。”
有人在冤狱铁窗内,梦见自己站在一片花海中,有个声音说:“有人记得你。”
还有人在战火纷飞中抱着垂死的孩子,耳边响起温柔低语:“别怕,我会陪你到最后。”
这些声音没有面孔,却让千万颗即将熄灭的心重新燃起微光。
十年过去,百年流转。
镇山不再是孤峰独峙,而成了万千善念汇聚之地。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自愿前来修行,他们不求长生,不争权位,只为学会倾听、理解与承担。学堂扩建至七重院落,教授的不是法术神通,而是医术、律法、农耕、织布、抚孤、安老等实实在在的济世之学。
每年秋分,所有弟子齐聚碑前,举行“归心祭”。仪式很简单??每人写下一件自己曾受过的恩惠,或做过的一件善事,投入湖中。纸笺入水即燃,化作金焰升腾,映照整座山脉。
这一日,恰逢陈昭之孙女登顶。她叫陈明漪,自幼体弱多病,却执意继承祖志。她捧着一株通体雪白的茯苓,在碑前跪拜良久,才轻声道:“我祖父救过九十三人,父亲救过一百零七人,我虽未能行走江湖,但在村中开设药堂七年,救治乡民一千二百余人。今日献此‘冰心茯’,非为求报,只愿先祖与镇山共鉴:陈家之诺,从未断绝。”
湖水静默片刻,忽而翻涌。金鲤再度跃出,这一次,竟有七尾并列而出,围绕少女游动一周,随后齐齐点头,潜入深处。不久,湖心升起一道虹光,凝聚成新的箴言:
**“信其所行,即是光明。”**
消息传开,四方震动。有大宗门质疑:“此等凡俗之举,岂能引动天地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