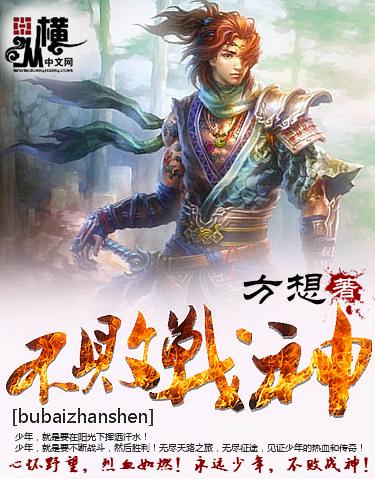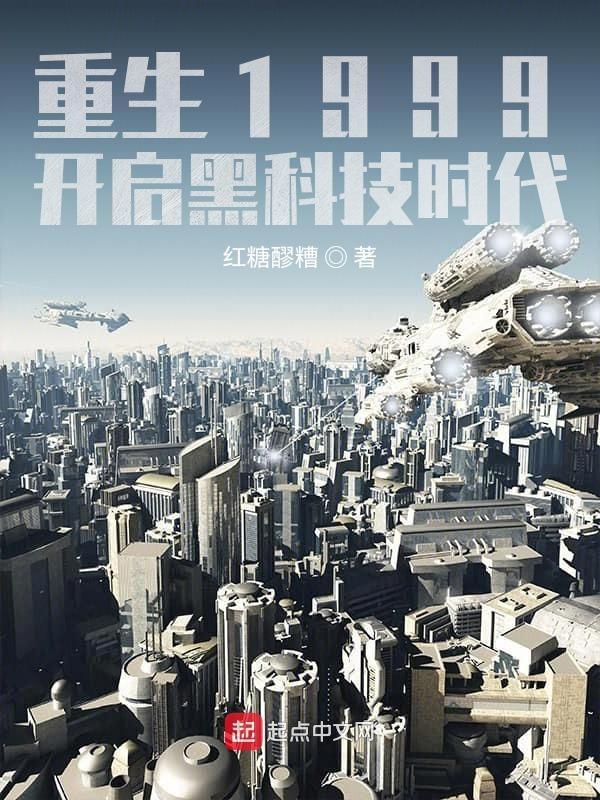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从送子鲤鱼到天庭仙官 > 第四百九十五章 黄粱武道(第2页)
第四百九十五章 黄粱武道(第2页)
“你做得很好。”母亲低声说,声音如风过竹林,“比我勇敢,比我坚定。我不曾教过你多少,可你却把我想说的话,替天下人说了出来。”
她抬起头,望向碑林之外那些沉默伫立的人们,轻声道:“你们也都听见了,是不是?”
众人无言,唯有泪水滑落。
母亲转身,面向金鲤所化的虹桥,抬手一引。顿时,无数光点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那是百年来所有通过归心阵传递的心声结晶,是那些未能出口的告别、无法送达的歉意、深埋心底的感激。它们如萤火飞舞,尽数涌入心山虚影之中。
心山震动,内部响起层层回音,仿佛千万人在同时低语。随后,一道新的碑文自山体浮现,环绕七字之外,成环形镌刻:
**“言不必达其口,心自有归途。”**
母亲的身影开始淡去。
临别前,她最后看了一眼女儿,微笑道:“现在,轮到你们继续了。”
光散,人消。
唯余铃声绕梁三日不绝。
三日后,新任主事道士召集全体弟子于碑前。他已年过六旬,鬓发斑白,眼神却比从前清澈许多。他没有讲经说法,也没有颁布戒律,只是取出照微生前用过的笔砚,铺开一张白纸,提笔写下七个问题,贴于碑侧:
一、你最近一次认真听别人说话,是什么时候?
二、有没有一句话,你一直想说,却从未开口?
三、你是否曾因害怕被误解,而选择沉默?
四、当你愤怒时,你是急于反驳,还是先听完对方?
五、你能否接受一个与你立场完全相反的人,依然值得被听见?
六、如果有人伤害过你,你还愿不愿意听他说完他的痛苦?
七、假如有一天你也无人可诉,你希望谁来听你说?
“这些不是考题。”他说,“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选择。”
自此,镇山不再设“接访日”,而是改为“静听日”。每逢初一、十五,弟子们便各自择地而坐,或立湖畔,或倚古树,或蹲碑角,手中不持法宝,不结法印,只备一杯清茶、一方手帕、一支笔。
来者若愿说,便坐下讲;若不愿说,便静静坐着。
有人哭了,递上手帕;
有人饿了,送上热粥;
有人醉酒胡言,也不驱赶,只等他醒来再说。
渐渐地,连其他宗门也开始效仿。
剑修放下杀伐之心,在山门口设“无刃亭”,专听仇家遗属控诉;
丹修建“静语庐”,收治因执念成疾的疯癫之人;
连一向冷漠的天机阁,也破例开放“心算台”,为人推演情绪因果,而非吉凶祸福。
更令人称奇的是,那尾金鲤并未随照微离去而消失。它仍在湖中游动,偶尔跃出水面,便会带起一段陌生记忆??某人前世曾在此地痛哭,某位修士曾在月下许愿永不伤人,某个孩子曾对着湖水说出第一个秘密。
人们开始相信:金鲤不是一条鱼,而是“倾听”本身所化的灵体,是归心之道的活见证。
又过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