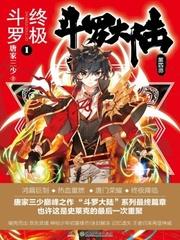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循规蹈矩能叫重生吗? > 305(第2页)
305(第2页)
那天下午,她独自去了趟墓园。
母亲虽健在,但她父亲已去世多年。碑前杂草已被清理过,显然有人定期来打扫。她放下一束白菊,轻轻拂去石碑上的尘灰。
“爸。”她蹲下来说,“我开饭店了,就在咱家老房子那边。你要是还在,肯定第一个冲进来嚷嚷‘给我留块肥的’。”
风吹动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回应。
“我妈还是倔脾气,嘴硬心软。我上次视频,她偷偷问我有没有按时吃饭,又装作不经意地说邻居家闺女结婚了,儿子抱孙子了……我知道她在担心我。”
她停顿了一下,声音微颤:“但我现在不怕了。我不再非得证明给她看什么,也不用靠粉丝数、收入榜、热搜位来告诉她‘你看,我没活得那么差’。我就在这儿,做着你觉得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事,可我觉得踏实。”
回程路上,她接到妇联李主任电话:“有个事得跟你商量。省里准备申报‘女性非遗技艺传承计划’,想把你妈的红烧肉技法列入地方传统美食名录。需要你提供完整的制作流程、家族传承证明,还有……你母亲本人的访谈录像。”
杜佳诺握紧手机:“我马上安排。”
第二天一早,她买了高铁票,直奔老家县城。
当她推开那扇熟悉的铁门时,母亲正蹲在院子里晒豆角。听见脚步声抬头,脸上先是惊讶,随即皱眉:“你怎么来了?店里谁看着?”
“请了两天假。”她放下行李,“我是来接你去做一件事的。”
“啥事?”
“告诉你做的红烧肉,快要进‘非遗’了。”
母亲愣住,手里的竹竿掉在地上。
“你说啥?”
“全省只有五个名额,评委会看了我们的纪录片,说这道菜背后有情感、有记忆、有代际传承的价值。但申报必须由传承人亲自出面讲述。”
母亲怔了半天,喃喃道:“就……就我家那口锅,也能算文化?”
“当然能。”杜佳诺握住她的手,“那是我小时候冬天放学最盼着的味道,是你一边骂我贪吃一边偷偷给我多捞一块肉的记忆。它怎么能不算?”
三天后,摄制组来到小县城。镜头前的母亲局促不安,反复问:“我要穿得好一点吗?”“话说错了会不会影响申报?”杜佳诺帮她整理衣领:“你就当对着我讲,像以前那样。”
采访开始。
老人坐在老屋堂屋的藤椅上,背景是斑驳的墙壁和褪色的年画。她慢慢说起六十年代饥荒年月,如何用一点点糖精熬出“假红烧肉”哄孩子开心;说起丈夫病重时,她每天炖一碗肉汁拌饭端到床前;说起女儿离家打工那年春节,她一个人守着冷锅冷灶,哭了整夜。
“后来她回来做直播,我以为她是作秀。”母亲望着镜头,眼角湿润,“直到看见评论区有人说‘我也想回家吃妈妈做的饭’,我才明白,原来她不是为自己,是替好多回不去的人,尝了一口家乡。”
拍摄结束,评委组成员集体鼓掌。一位白发专家走到杜佳诺面前:“你知道为什么我们选这个项目吗?因为它不是表演出来的温情,而是从生活深处长出来的根。”
一个月后,公示名单发布:**岳阳杜氏红烧肉制作技艺**,成功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消息传来那天,“佳诺食堂”挂起了红灯笼。街坊们自发送来鞭炮,孩子们围着拍照。周明远拍下这一刻发到社交平台,配文只有六个字:“**她做到了。**”
深夜打烊后,杜佳诺翻出母亲寄来的那罐剁辣椒,打开盖子闻了闻,辣香扑鼻。她拿出手机,点开收藏夹里那段名为《我女儿做饭的样子》的视频,又一次点开播放。
画面中年轻的自己系着围裙,认真讲解火候与调味,眼神明亮,语气温柔。四十三遍,她终于明白,那不是一个母亲对成功的骄傲,而是一个女人对女儿归来的等待。
她写下一条私信:
>妈,红烧肉进非遗了。
>他们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可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