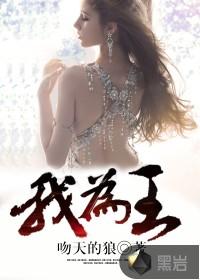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1994:菜农逆袭 > 第444章 岭南冬蔬翘楚(第3页)
第444章 岭南冬蔬翘楚(第3页)
声音传遍山谷,惊起一群白鹭。
当天下午,一辆军绿色吉普驶入村庄。车上下来一位穿旧夹克的中年男人,提着一个铁皮箱。他径直走向张立,敬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我是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退役工程师李卫国。”他说,“我爹是敦煌莫高窟最后一任壁画修补匠。家里传下来一份唐代《耕织图》残卷,背面记录了十六种西域古作物名称。我一直以为是传说,直到看到你们平台的信息……”
他打开铁箱,取出几个用油纸层层包裹的种子袋。
“这是‘大宛紫麦’‘龟兹火豆’‘楼兰香糜’……据说是张骞带回的品种。我在戈壁滩试种了八年,死了七次,第八年才活下来一片。”
张立双手接过,指尖微微发抖。
他知道,这条路,已经通向历史深处。
十月五日,平台正式开启“丝路归种计划”。沿着古代商路,向新疆、青海、宁夏等地派遣护种特使,寻找那些湮没在风沙中的农业文明遗珠。一支科考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废弃驿站下,发掘出一座唐代种子窖,其中部分小麦样本经碳十四测定已有1270年历史。虽无法发芽,但基因测序显示其具备极强耐盐碱特性,或将为现代育种提供关键片段。
十月十日,教育部宣布将“乡土种子复兴工程”纳入中小学劳动教育必修内容。教材编写组专程来到李家湾,邀请张立担任顾问。他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课本里要有一页空白,让孩子自己画下他心中最重要的那一粒种子。”
冬天悄然临近。
十一月初,北方首场寒潮来袭。许多传统农户开始焚烧秸秆取暖,浓烟滚滚。张立立即发起“禁烧保卫战”,组织团队下乡推广“秸秆生物炭还田技术”??将秸秆低温碳化后混入菌剂,制成高效缓释肥。
一位老农质疑:“烧了省事,你还搞这么多弯弯绕?”
张立没解释,只带他去看一块对比试验田:左边是焚烧后的焦土,板结发硬;右边是施用生物炭的地块,松软黝黑,蚯蚓穿梭。
“你烧掉的是土地的命。”他说,“我们烧的是柴,伤的是根。”
老农沉默良久,最终扔掉了火把。
十二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召开生态文明建设座谈会。张立受邀发言。会议结束时,一位白发官员悄悄递给他一份文件复印件。
“内部消息。”那人低声道,“明年两会将提交《民间种质资源保护法》草案,明确赋予农民留种、交换、传播传统品种的权利,并设立专项基金支持社区级种子银行。”
张立捏着纸张,手心出汗。
他知道,这场始于一捧土、一粒种的逆行,终于撬动了制度的齿轮。
年末最后一天,李家湾举办跨年守夜。
全村人在晒场上围坐,篝火熊熊燃烧。孩子们轮流讲述自己这一年见过的种子故事。有个小男孩说他在贵州看见一棵三百年的古茶树,树洞里藏着蜂巢形的种子囊;有个小姑娘说她爸爸从黑龙江带回一包“闯关东小米”,是曾祖父当年挑担走西口时随身携带的。
午夜钟声敲响时,张立拿出那只火种陶瓮,轻轻打开。
“我们曾说要把种子封存。”他望着众人,“但现在我想通了??真正的保存,不是锁起来,而是播下去。”
他将陶瓮倾斜,万千种子如星河流泻,落入事先准备好的分装袋中。
“明年春天,每人带十粒走。种在你的家乡,你的阳台,你的学校后院。不管成败,只要有人记得,它们就活着。”
风起了,带着雪的气息。
远处,新架设的气象站显示屏上跳出一行字:
**今日地温:4。3℃。
深层菌群活性:稳定。
休眠种子数量:监测中。**
张立抬头望向星空。
北斗七星清晰可见,像一把悬挂在天际的犁。
他知道,冬眠的土地正在酝酿春天。
而他们播下的,不只是种子。
是信念,是记忆,是无数个未来可能重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