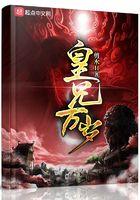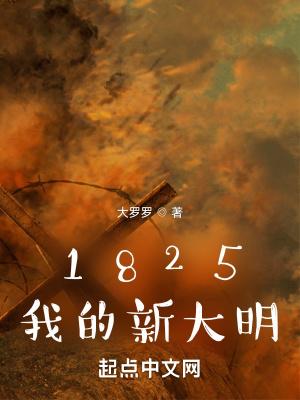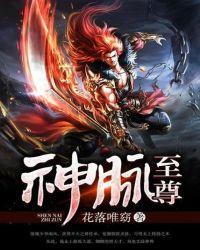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我和五个大美妞穿越到北宋 > 第三百九十九章 宋江跟对了人(第3页)
第三百九十九章 宋江跟对了人(第3页)
北方边关,那位曾哼出《归墟调》的老塾师,第一次开口说话:“孩子们,今天我要教你们唱一首歌,名字叫《光》。”
大理悬崖上,游方道士腰间玉佩恢复平静,裂纹愈合,星图转为金色。他仰天长笑:“她赢了。”
开封皇宫内,赵桓正在批阅遗诏修订稿,忽然案头烛火再次摇曳,这次拼出的却是五个字:
>**“她们还在。”**
他怔住,随即起身走向庭院,望着东方晨曦初露,久久不语。
而在西域某处绿洲,戴帷帽的女子停下脚步,再度举起铜铃。
这一次,她没有摇响。
只是轻轻抚摸铃身,低语:“阿阮,谢谢你替我们走完最后一程。”
数日后,阿阮被人发现倒在乐坊废墟外,气息微弱。一群流浪艺人将她救起,带回村落。她昏迷了整整七天,醒来时第一句话是:
“告诉所有人,《归墟调》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在孩子的笑声里,在恋人相拥的呼吸中,在工匠敲打铁器的节奏里,在农夫耕田时哼的小调里。”
“去找它吧。不要等奇迹降临,你们自己就是奇迹。”
从此,江湖上多了一句民谣:
>“风不起,铃不响;
>心若动,鹤自翔。
>不认命者终自由,
>孤影亦能照大江。”
多年后,有人在敦煌石窟最深处发现一幅壁画:画面中央是一架银色风隼,正冲破云层。下方五位女子并肩而立,容貌依旧模糊,但第六人站在她们身后半步,手执骨笛,面向夕阳。
画旁题字仅有一句:
>“第六声,来自沉默之人。”
据说,每当国家陷入危难、人心麻木之时,总会有某个无名少年或老妪,在寂静夜里吹响一段陌生旋律。那音色既不像笛,也不像箫,倒像是大地深处传来的心跳。
听到的人,往往会流泪,然后做一件很久不敢做的事??比如辞去高官,返乡教书;比如撕毁密报,放走囚犯;比如握住仇人的手,说一句“我原谅你”。
没有人知道这声音从何而来。
但每一个选择善良与真实的人,心里都清楚:
**她一直都在。**
就像春天总会回来,就像黑夜终将迎来黎明。
就像那面写着“声即自由”的旗帜,即使被战火焚毁,也会有人用血与布重新缝制,挂上城头,迎风招展。
而戈壁滩上的五朵野花,依旧年年盛开。
清明时节,风过之处,铜铃轻响。
一声鹤唳,划破长空。
仿佛在说:
“别忘了,你也曾说过??
**我不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