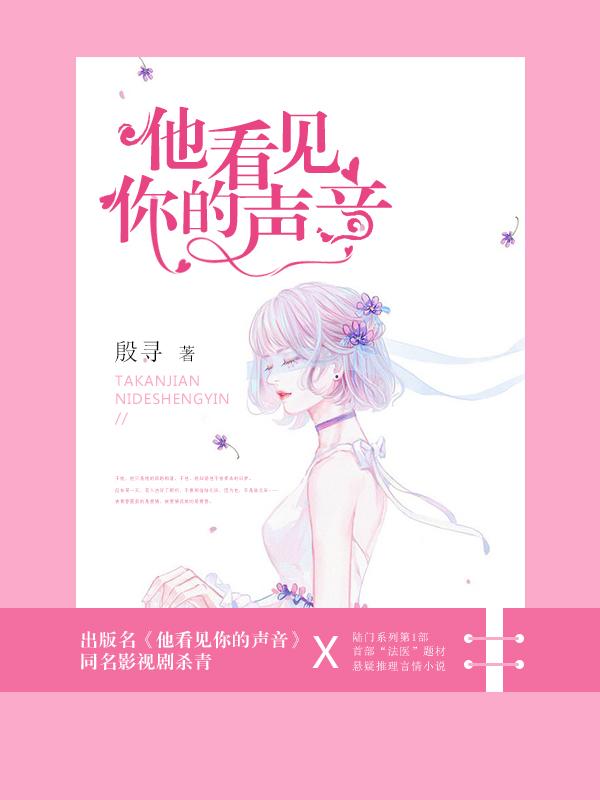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文娱2000:捧女明星百倍返利 > 第414章 天真好骗斯嘉丽公平快乐的选角(第1页)
第414章 天真好骗斯嘉丽公平快乐的选角(第1页)
这帮女人,得到了一个消息觉得不够。
想要继续追问,林志铃推说自己知道的不多。
她们纷纷给唐文打电话,想要通过今晚来贿赂他,以便获悉明天的“比试”题目。
被唐文辞严义正地拒绝了:“这次。。。
夜色如墨,洒在青海湖畔的盐碱地上,月光映出一圈圈泛白的涟漪。风从湖面吹来,带着咸涩与寒意,掠过一排低矮的帐篷。帐篷外,三台记录仪静静立着,镜头朝向湖心方向,像守夜的哨兵。远处,鸬鹚捕鱼人达瓦正蹲在岸边修补渔网,手指粗粝,动作却极稳。他不说话,只是偶尔抬头看一眼天,仿佛在等什么。
文弟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裹着一件旧军大衣,手里捧着一杯早已凉透的酥油茶。他没有打扰达瓦。他知道,这一代的鸬鹚捕鱼人,是最后一批真正懂得“听水声辨鱼群”的人。再过几年,年轻人不愿继承这门手艺,政府也因生态保护限制捕捞,这项延续了六百年的传统,注定要沉入记忆深处。
但今晚不同。
达瓦忽然放下渔网,站起身,走向湖边那艘破旧的小木船。他拍了拍船头一只年迈的鸬鹚,低声说了句什么。那只鸟歪了歪头,竟缓缓张开翅膀,发出一声悠长而沙哑的鸣叫。紧接着,其余十几只鸬鹚纷纷振翅,齐声应和。声音在空旷的湖面上回荡,像是某种古老的召唤。
文弟屏住呼吸。
达瓦转过身,看向他:“你不是想听‘水语’吗?今晚月亮正好,鱼群来了。”
文弟愣住:“你说……它们会回应?”
“不是回应我,”达瓦摇头,“是回应这片湖。我们祖辈传下来的歌,本就是唱给鱼听的。它们听得懂。”
他走到一台记录仪前,蹲下,轻轻抚摸冰冷的金属外壳:“我知道你在录。没关系。但你要答应我??如果以后没人再唱这首歌,至少让机器替我喊一声:‘鱼啊,我还在等你。’”
文弟点头,喉咙发紧。
达瓦登上小船,将鸬鹚一只只系上绳索,然后划桨入湖。月光下,他的身影渐渐模糊,只剩下一串轻微的水声。突然,他开口唱了起来。
那是一段没有任何旋律结构的吟诵,音调忽高忽低,像风穿过岩缝,又像浪拍打礁石。歌声并不悦耳,甚至有些刺耳,但却有一种奇异的节奏感,仿佛与湖水的波动同步共振。随着歌声响起,湖面竟开始出现细微的骚动??成群的小鱼从深水处涌向浅滩,水面泛起密集的涟漪。
文弟盯着监视器屏幕,心跳加快。数据分析模块自动捕捉到音频波形,显示出一种从未见过的声频模式:低频段密集震荡,高频段则呈现出规律性的脉冲,与周围环境噪音完全分离。系统标注:“疑似生物性声波引导行为。”
他忽然明白??这不是民谣,而是一种**声学驱鱼技术**,是千百年来渔民通过观察、试错、传承下来的经验科学。他们用嗓音模拟特定频率的震动,干扰鱼群的侧线感知系统,从而引导其移动路径。这种知识从未写进书里,也不属于任何学科体系,但它真实存在,并且有效。
两个小时后,达瓦归来,船上满载鲜鱼。他笑着把一条肥美的湟鱼递给文弟:“送你。记住,这不是征服,是商量。我们和鱼,都是湖的孩子。”
那一夜,文弟没睡。他在帐篷里反复回放那段录音,逐帧分析声波图谱。凌晨三点,他拨通唐文娴的电话。
“我要做一件事。”他说,“把‘真实数据库’扩展为‘真实语言库’。”
唐文娴沉默片刻:“你是说……收录所有非标准语言形态?”
“不止。”文弟声音坚定,“包括动物交流、自然节律、手工技艺中的隐性知识、甚至是哭声、叹息、咳嗽里的信息密度。人类的语言,从来不只是文字和语法。那些说不出口的,才最接近真实。”
唐文娴轻叹:“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存储量将是现在的百倍,解析难度近乎无限。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这是疯子的幻想。”
“可巴合提的歌能传下族谱,独龙江老人能靠纹面记住亲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相信,一段咳嗽里藏着疾病的密码,一句叹气里埋着时代的重量?”
电话那头长久静默。最终,她只问了一句:“需要我做什么?”
“联系中科院声学所、民族语言研究所、还有聋哑教育中心。我们要组建一个跨学科团队,目标只有一个:破译‘沉默的语言’。”
挂断电话时,东方已泛起鱼肚白。文弟走出帐篷,看见达瓦正蹲在火塘边煮鱼汤。袅袅炊烟升腾而起,与晨雾交融。
“你昨晚录的东西,能给我看看吗?”达瓦问。
文弟递过平板。当那段歌声响起时,老人闭上了眼,嘴角微微抽动。
“我父亲也这么唱过。”他喃喃道,“他说,等哪天唱不动了,湖就会忘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