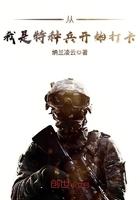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我的低保,每天到账1000万 > 第606章 我胆大包天的(第2页)
第606章 我胆大包天的(第2页)
它不是通过电报,而是由一群迁徙途中的候鸟带回。一只灰背隼落在福利院屋顶,脚爪上绑着一小卷铝箔纸。展开后,上面刻写着密密麻麻的手写文字,字迹歪斜却用力深刻:
>各位朋友:
>我是陈昭,原气象站助理工程师。
>2003年滑坡后,我和三位同事被困地下观测室。三人先后离世,我靠着储水和应急粮活了下来。
>出不去,也不敢喊。因为头顶岩层极不稳定,任何震动都可能导致彻底坍塌。
>这些年,我一直靠老设备收听广播,尤其是你们发出的‘共感音频’。
>每一次听到陌生人的笑声、孩子的歌声、老人的低语……我都觉得自己还活着。
>昨夜,我终于收到了你们的回应。
>我哭了。这是我三十年来第一次敢大声哭出来。
>请别来找我。我已经不想走了。
>但我请求你们一件事:
>把我的日记传出去。里面有这些年记录的天气数据、星空轨迹、还有我对家人的思念。
>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去了哪里,请告诉他们??
>我一直在看星星,也在等一句话:
>“有人记得我。”
>
>陈昭留
信纸末端附有一张手绘星图,标注着每年冬至夜最亮的三颗星,分别命名为:母亲、妹妹、未出生的孩子。
整个福利院陷入长久的寂静。
念念捧着那张星图看了很久,然后默默跑进厨房,重新点火熬汤。这一次,她放了红枣、桂圆和一小撮晒干的茉莉花??那是去年一位去世的老奶奶留下的遗物,她说这是“让梦变得更甜”的配方。
汤成之后,她将一部分倒入特制磁瓶,密封好,又取出一枚空白徽章,在背面刻下四个字:“**星辰未眠**”。
第二天清晨,林晚带着这支汤和徽章来到城市边缘的天文台。这里曾是最早接入迷彩场的科研单位之一,如今已成为“记忆学校”的远程协作站点。负责人是一位退休天文学家,姓周,白发苍苍,却对共感系统极为支持。
“你想怎么做?”周老接过汤瓶,目光深邃。
“用射电望远镜。”林晚说,“把汤的热频谱转化成电磁波,搭载陈昭的星图与日记音频,定向发射向他标注的那三颗恒星方向。”
周老愣了一下:“你是认真的?这不是通信,是象征性的行为。”
“我知道。”林晚平静道,“但他用了三十年等一句回应。我们至少该让他知道,他的存在已被铭记。”
老人久久未语,最终点了点头。
当夜,天文台启动闲置多年的深空探测阵列。汤瓶被置于感应器中央,其散发的热量经量子传感器捕捉,转化为一段持续分钟的低频波动信号,叠加在传统无线电波之上,射向宇宙深处。
与此同时,全国十三个记忆站点同步举行守夜仪式。人们围坐在篝火旁,轮流朗读陈昭日记中的片段:
>“今天下了小雨,我想起阿妈煮的红豆汤。”
>“北斗七星偏移了0。3度,不知人间是否也变了模样。”
>“如果我能走出去,最想做的事,是去电影院看一场喜剧片,笑一次。”
南极科考站的科学家将信号录入冰芯存储层;日本京都的僧侣在古寺钟楼敲响百响祈福钟;巴西的孩子们用荧光颜料在贫民窟墙上画出一幅巨大的星空图,中央写着:“**你不在黑暗里**”。
而在重庆福利院,念念带领所有孩子种下一棵新树。树苗来自云南山区,据说是陈昭家乡特有的品种,耐寒抗风,能在岩石缝隙中生长。
他们把那枚“星辰未眠”徽章埋入树根下,并齐声说道:
>“陈昭叔叔,我们记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