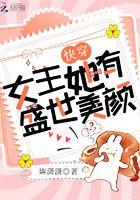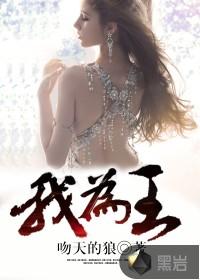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这个明星正得发邪 > 第432章 唱红歌算什么本事(第2页)
第432章 唱红歌算什么本事(第2页)
孙恺抬头望向黄河。夜色中,河水依旧奔流不息,黑黢黢的水面映着残存的星光。
“你觉得,黄河为什么千年不息?”他反问。
陆燃摇头。
“因为它底下有岩浆。”孙恺缓缓道,“表面看是水在流,其实是大地深处的火在推着它走。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表面上歌舞升平,可真正支撑它的,是苦难、抗争、牺牲和记忆。这些东西埋得太深,久而久之,人们就忘了它们的存在。可一旦有人把它挖出来,点燃,就会烧得整个时代都颤抖。”
他转过身,目光灼灼:“所以我必须唱。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那些已经说不出话的人。为了那些死在战场上、饿死在逃荒路上、默默无闻却撑起家国脊梁的普通人。他们不该被遗忘。”
风掠过河面,吹动他的白发。那一瞬间,陆燃觉得他不像一个歌手,倒像一座伫立千年的碑。
“接下来呢?”赵龙棠轻声问,“您打算做什么?”
孙恺沉默片刻,从怀里掏出一张泛黄的乐谱复印件,递给陆燃。
陆燃接过一看,标题写着:《长江组歌?第一乐章:川江号子》。
“这是……”
“我下一个计划。”孙恺淡淡地说,“长江比黄河更长,流域更广,故事更多。我要沿着六千三百公里的长江,收集民谣,采访渔民、纤夫、码头工人,写一部属于长江的交响诗。不靠资本,不靠平台,只靠一群愿意相信音乐力量的人。”
陆燃猛地抬头:“您要巡演?”
“不是巡演。”孙恺纠正,“是行走。一边走,一边唱,一边教。我会找一百个青年音乐人,组成‘长江行吟团’,每到一地,就教当地人唱自己的歌,录下来,传出去。我们要让这条江的记忆,重新活过来。”
赵龙棠眼睛亮了:“我可以加入吗?”
孙恺看着她,笑了:“你早就加入了。你以为我为什么会选你唱《黄河颂》?因为你眼里有光。不是明星的光,是土地的光。”
陆燃忽然感到一阵热血涌上心头。他握紧手中的乐谱,声音有些发抖:“那……我能跟吗?我不懂音乐,但我能拍,能写,能传播。我不要钱,只要一个位置。”
孙恺盯着他看了许久,终于伸出手:“欢迎加入。不过提醒你,这条路没有热搜,没有打赏,可能几年都不会有人关注。”
“可一旦爆发,就是燎原之火。”陆燃握住他的手,用力点头。
就在这时,远处一辆黑色轿车缓缓驶来,在舞台前停下。车门打开,走出一个戴墨镜的中年男人,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
“文化部的。”赵龙棠低声说。
那人走近,摘下墨镜,神情肃穆:“孙老师,我是文艺司副司长陈国栋。上级指示,希望您能接受一次内部座谈,谈谈《黄河小合唱》的创作过程和后续规划。”
孙恺不动声色:“座谈会可以开,但我有两个条件。”
“您说。”
“第一,全程公开直播,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审查删减;第二,我要带陆燃和赵龙棠一起参加。他们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不能被排除在外。”
陈国栋微微一怔,随即点头:“我尽力争取。”
“不必争取。”孙恺平静地说,“如果做不到,那就没什么好谈的。音乐不是谈判筹码,它是人民的呼吸。”
对方深深看了他一眼,最终说道:“明天上午九点,文化大厦会议室。直播的事……我们会安排。”
待车子离去,陆燃忍不住问:“您真敢这么硬刚?”
孙恺笑了笑:“他们怕的不是我唱歌,是怕我说真话。可只要我还站得起来,就得说。”
夜更深了。
三人并肩坐在石阶上,望着黄河。水流声低沉而恒久,如同大地的心跳。
“你知道吗?”孙恺忽然说,“二十年前,我也坐在这里,想过放弃。那时候流行偶像当道,主旋律没人听,严肃音乐被视为‘老古董’。我的专辑卖不动,音乐会没人看,连学生都不愿学美声。我问自己:是不是该顺应时代,改唱情歌,包装自己,赚快钱?”
他顿了顿,声音轻了下来:“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位老船工。他已经七十多岁,腿脚不便,却坚持每天来河边走一趟。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爹是船夫,我爷是船夫,我家三代都在这条河上讨生活。我不来,谁还记得他们?’”
“那一刻,我哭了。”孙恺仰头,眼中闪着微光,“所以我决定,哪怕只剩一个人听,我也要把这些歌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