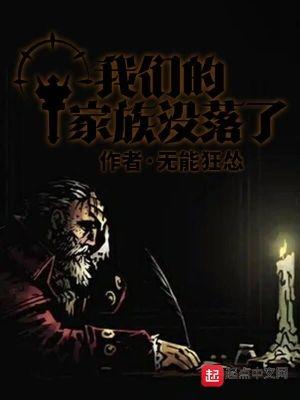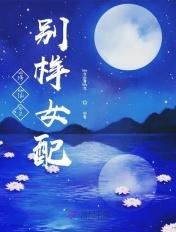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说好当闲散赘婿,你陆地神仙? > 第270章 偷鸡不成蚀把米求月票(第2页)
第270章 偷鸡不成蚀把米求月票(第2页)
少女眼泪夺眶而出,展开布帛,上面用炭条歪歪扭扭写着一段话:
>“我娘叫阿?,十年前为救落崖采药人摔断双腿,族长说她坏了规矩,不准人提她名字。可我想记住她……哪怕只有一个人知道也好。”
苏禾接过布帛,久久无言。次日清晨,她在寨中空地上支起一方木板,用朱砂笔写下“阿?”二字,并附上救人经过。围观族人起初惊惧退避,认为此举触犯祖训,但当他们看到少女跪在木板前痛哭呼喊“娘”时,不少人眼中泛起了泪光。
第三日,又有两位老人拄拐而来,带来另一块破旧布片,上面写着两个名字:一个是“岩桑”,曾在饥荒年开仓放粮;另一个是“依兰”,曾冒死掩护逃奴婴儿。
苏禾一一记录,挂在寨口。
到了第七天,整个山寨竟自发组织起来,每户人家都拿出珍藏的布帛或竹简,写下自己家族中曾做过善事却从未被提及的亲人名字。短短半月,寨口挂满了数百条“忆名幡”,风一吹,猎猎作响,宛如灵魂在低语。
族长终于坐不住了,带人闯入苏禾住所,怒斥道:“你们扰乱祖制!这些名字本该遗忘!”
苏禾静静看着他,反问:“那你记得你父亲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族长一怔。
她继续道:“据我所知,你父名唤‘勐戈’,年轻时曾为保护全寨水源,孤身深入毒瘴林斩杀妖蟒,归来时全身溃烂,三日后离世。那时全寨人为他守灵七日,连敌对部落也送来祭品。可如今,除了几位老人,还有谁记得勐戈?他的名字,是不是也快被人忘了?”
族长脸色骤变,嘴唇哆嗦。
苏禾站起身,一字一句道:“你们怕的不是记住,而是害怕一旦开始记住,就再也无法掩盖那些被刻意抹去的真相。可若连善都被禁止提起,恶岂非更加肆无忌惮?”
人群寂静无声。
良久,族长缓缓跪下,对着木板磕了一个头,哽咽道:“我……我也想记得我爹。”
从此,哑岭改名“启音寨”,意为“沉默终将开口,记忆自此回响”。寨中设立“念亲堂”,专供族人追述先辈善行。三年后,此地竟成为西南诸蛮中最重仁义之地,连邻近部族也都慕名前来学习“记名之道”。
而苏禾,依旧踏上征程。
她走过草原,调解牧民与商旅之间的百年仇怨,靠的不是武力,而是一本厚厚的手抄册子??里面记录着双方祖先曾互赠牛羊、共抗风雪的往事;她进入皇城边缘的贫民窟,在废墟中建起第一座“忆屋”,召集流浪儿围炉夜话,教他们写下“谁曾给我一口饭”、“谁在我冻僵时脱下外衣”。
有人不解:“这些孩子连字都不会写,记这些有何用?”
她答:“正因为不会写,才更要学。一个名字,就是一束光。你不教他们写,谁来照亮他们的黑夜?”
十年间,全国兴起“忆屋运动”,由承恩者自发组织,遍及城乡角落。孩子们在那里学会识字,也学会感恩;成年人在那里倾诉过往,重建信任。许多曾经犯罪之人,在讲述自己曾受何人救助后痛哭流涕,自愿投案悔改。司法官员惊呼:“这不是教化,这是心灵的审判。”
而在所有忆屋的墙上,都挂着同一幅画像??并非苏禾本人,而是一位普通女子的侧影,怀抱琵琶,背对朝阳,题字仅有一句:
>**“她不曾拯救世界,但她教会我们如何记住。”**
这一日,苏禾回到栖凰谷。
山谷依旧静谧,昆仑井封印已稳,唯有一缕淡淡的愿力之气萦绕不散。她在井边坐下,取出琵琶,指尖轻拨,《忆平生》的旋律再次响起。
音波荡开,竟引动地下古脉共鸣。片刻后,井口浮现出一行虚幻文字:
>“检测到第三代传火者回归,系统重启。”
>“请选择:开启‘神启模式’,或延续‘凡人之路’。”
柳浪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手中端着一碗药汤,淡淡道:“你还敢回来?上次选择‘凡人之路’,差点让整个愿力建构崩塌。”
苏禾回头一笑:“可它没崩,反而更稳了。”
柳浪坐下,递过药汤:“我知道你会选什么。就像当年你宁愿散尽修为,也要把最后一口元气注入井底,只为让更多普通人能被记住。”
她接过碗,轻啜一口,眉头微皱:“这药……怎么比以前苦多了?”
“加了忘忧草。”他平静地说,“如果你决定再次放弃力量,至少让我帮你忘记一些痛苦。”
苏禾摇头,将药碗放在一旁:“我不需要忘记。每一滴泪,每一次心痛,都是信的一部分。若连痛都忘了,还谈何信念?”
她伸手抚过琵琶弦,低声说:“我选‘凡人之路’。”
空中文字应声而变:
>“指令确认。传火机制永久锁定为‘群体记忆驱动’。”
>“警告:此后再无个体可凭愿力成神,唯有万民心念凝聚,方可短暂显现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