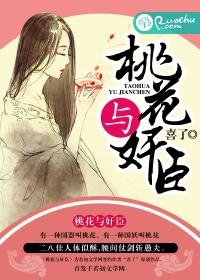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青袍映沧澜 > 春和她胸有丘壑(第3页)
春和她胸有丘壑(第3页)
扶登秦心底那股愤怒依旧燃烧,却又悄然渗入一丝同为女子、对另一种无形枷锁的沉重悲悯。
同一时间·萧氏临时库房外
临时搭建的凉棚勉强遮挡着午后略显刺目的光线。
萧春和端坐其中,身姿笔挺如尺量过,天水碧的云锦裙摆在简陋的木凳上铺开,依旧纤尘不染。
她面前摊开两份东西:一份是扶登秦那份改良铆钉的手札图纸副本,墨线清晰,标注严谨;
另一份则是新送来的工料采买单,墨迹未干,上面“足料足工”几个字下,紧跟着一串令人心惊肉跳的数字。
萧春和洁白指尖点在采买单上,沿着那串长长的、代表着巨额白银消耗的数字缓缓滑下。
她那秀气的眉几不可察地蹙紧了一瞬,随即又舒展开,快得像从未出现过,只余下眼底一片如同计算最优解般的考量。
这成本,远超预期,几乎要蚀掉这趟皇差的利润。
她心中默算着,如何从别处挪补,如何在向太子陈情时,将这“损失”转化为更重要的“忠诚”与“顾全大局”。
萧景明站在一旁,指挥着仆役将第一批按“原版”要求、不惜工本赶制出来的新铆钉小心搬入库房。
那些铆钉泛着冷硬纯粹的金属光泽,沉甸甸的,与之前断裂的劣品天壤之别。
然而,他的目光却有些飘忽,时不时越过杂乱堆放的工料,投向巫工驻地深处,尤其是那顶属于扶登秦的低矮小帐。
萧景民眉宇间的烦躁与憋闷,全然被姐姐看在眼里。
萧春和清泠泠的声音道破他的心思:“还在想那位扶工正?”
萧景明猛地回神,脸上掠过一丝被看穿的狼狈,随即化为更深的烦躁和不忿:“阿姐,你说她……她怎么就那么轴?明知去问太子殿下也未必能讨到好,甚至可能……”
他咽下了“自取其祸”几个字,语气急促地说:
“萧氏认罚,工料也按她的要求重做了,还不够吗?非要揪着那个所谓的‘解释’不放!”
萧春和从图纸上抬起眼。
她那双沉静的眸子看向弟弟,带着洞悉世情的审视,仿佛在评估一件商品的价值波动,又或是在分析一场棋局的走向。
萧春和平静无波的说道:
“你觉得,她仅仅是为了阿桃的腿,或是她自己受伤的手?”
萧景明烦躁地扯了扯束发的赤金发带:
“不然呢?”
“她难道还想凭一己之力,撼动东宫不成?”
萧景明无法理解那种近乎飞蛾扑火的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