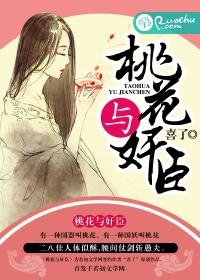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女相冬辞 > 暗箭伤人(第1页)
暗箭伤人(第1页)
林融霜本为着今日元珵撺掇着孟冬辞不带她去刑场一事在自个儿屋里生闷气,可眼看着午膳时辰都过了许久,还不见他二人回来,有些心急,便踱到正门处去迎。
不想才到正门,还没转过照壁,便迎头叫柳莲撞了个趔趄。
“莲姨?你不是……”
“林姑娘!”柳莲一把抓住她的手:“殿下与皇子妃在门口遇刺!”
林融霜跨出大门的时候,孟冬辞正搀着元珵躲在马车与院墙撑出的死角处,元珵一身鸦青衣裳瞧不见血,倒是孟冬辞手上脸颊连着外头那件月白的斗篷都沾了血。
“阿姐!你伤哪儿了?”
“我没事,”孟冬辞朝林融霜摇头,偏头看向已没了意识的元珵一眼,“他为护我受了一处箭伤,可如此快便昏迷,那箭恐怕有问题。”
林融霜闻言蹲下身查看。
元珵伤在右肩,自背后没入,从身前锁骨旁穿出。
“血不见黑紫,这就是普通的弓箭,可穿身而过,说明射箭人应该离得极近,”林融霜站起身,此腰间抽出短剑,“阿姐,我去追!”
“不追。”孟冬辞摇头。
上回陆羽说过,他们在别院周围留了人看顾元珵,刺客离得这么近射出此箭,若功夫不济,不会是陆羽他们的对手,若是身手很好,林融霜独身一人贸然追上去,恐有危险。
“在此处动手,他们想杀的是我,”孟冬辞朝林融霜伸手借力,“元珵现下有绢册和金矿做保命符,无论背后的人是谁,都会有所顾忌,咱们与他待在一处才安全,先回院里替他治伤。”
话音落,柳荷柳莲已带着小厮赶来,将他们迎进了院,吩咐闭门落锁。
朱门闭合后,别院斜对面,一棵落满雪的马尾松抖了两抖,一个裹着白色斗篷的人与积雪一道落地,他将手里的长弓和箭篓随手扔到旁边的无人看守的夜香车上,拉下兜帽,转身隐入街巷熙攘的人群中。
阵风拂过,斗篷之下,露出赭色袍摆的一角。
倾脚头拎着桶回来时,见车上多了东西,一头雾水地拾起,高声问:“谁的弓箭落这儿了?”
见周围无人应他,便又拎起那不知什么皮子缝成的箭篓打量,见上头溅着什么东西,凑近闻了闻:“腥,好像血?”
这箭篓瞧着不旧,那皮子应该能换些银钱,倾脚头四下看了一圈,见没人注意,便将长弓和箭篓掖进木桶中间,推着车走了,走出两步,又咦了一声,嘟囔道:“闻着像血,可血怎么是黑的呢?”
*
孟冬辞虽通些药理,但拔剑清创却断然不会,请的郎中还没到,林融霜也说那箭没毒,她便想以元珵房中的创药替他止血,可那药粉倒了三回,将前后伤口都糊了一层,却不见血有止住的迹象。
他伤在肩头,不好躺,只能置了凭几给他倚着,刚进屋时他本醒了一会儿,睁眼时孟冬辞正拿着把剪子剪他的衣裳,见孟冬辞没伤着,便放下心,强撑着笑说:“这是上回你遇险我不在场,老天看不下眼,变着法儿叫我还你这伤呢,娘子瞧瞧,和你上回伤的,可是同一个地方?”
“咱们也真是有夫妻缘分,连遇刺都伤在一个地方,娘子你……”
孟冬辞眼没抬便打断他:“闭嘴。”
血止不住,孟冬辞本就急,掌心全是冷汗,元珵又偏要挑这时候与她贫嘴,便又没好气的说:“也不是三岁孩子,整日信这些没用的缘法,受个伤也能扯着往上贴,有这个力气,不如闭眼养养精气神儿。”
话音落了半晌也不见元珵还嘴,她觉得奇怪,一抬眼,便见元珵又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一处寻常的箭伤,怎会叫他虚弱至此?
又等了一盏茶的时候,柳荷才领着郎中回来,孟冬辞一抬眼,好巧不巧,又是上回她遇刺时那个战战兢兢的老郎中。
因而苦笑问道:“咱们这别院前儿遣走了宫里拨来的太医,倒是劳动您一次次赶来救命,您如何称呼?”
老郎中一进来见屋里除了一个不省人事的元珵外全是女眷,便又吓得躬身垂首:“不敢,老朽姓尚,单名崇。”
“尚老,”孟冬辞自榻边站起身让开一条路,“殿下中了暗箭,我按寻常的法子止血未能见效,想着或许以针封穴或能行,劳您为他拔箭止血。”
尚崇点头,一头吩咐准备净水油灯之类,一头开了医箱,自里头取了银针。
如孟冬辞所料,前后下了银针,先前不断渗血的伤口果然有好转之象。
“这像是将箭头用什么泡过,叫伤口凝不住血,”她一头看着尚崇掰断箭尾准备给元珵拔箭,一头问林融霜,“你先前可遇见过类似的法子?”
没听着林融霜答她的话,孟冬辞转身去瞧,见她正蹲在地上研究那把被暗箭劈坏了的琵琶,便又喊了她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