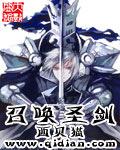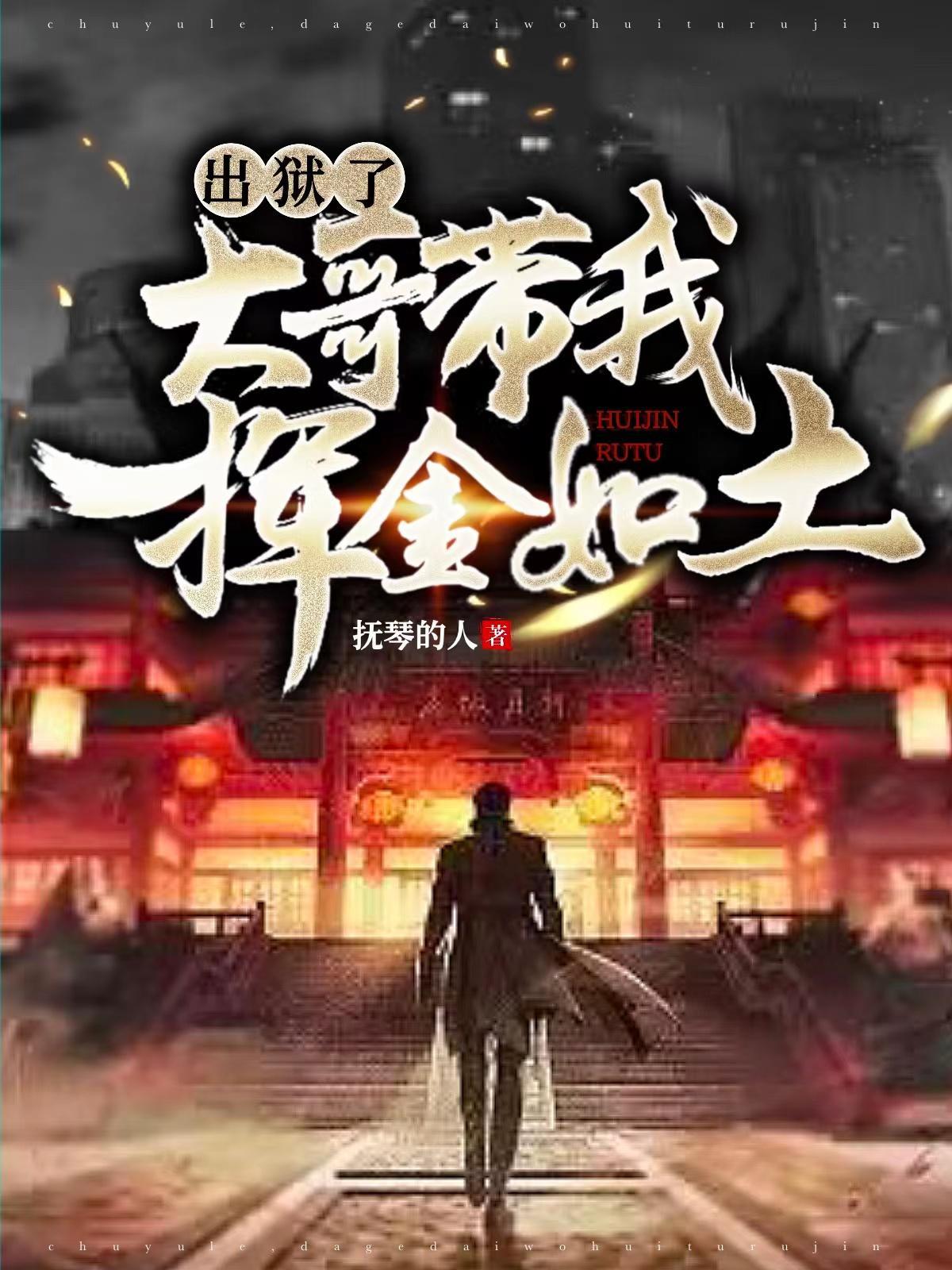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刑警日志 > 第1912章 周边走访调查(第2页)
第1912章 周边走访调查(第2页)
>所以,作为刑警,我们必须比罪犯更细心,比谎言更执着,比时间更不愿妥协。
>因为我们手中握着的,不只是案件编号,更是某个人的人生,某个家庭的夜晚,某段历史的真实。
>此案教会我的,不是如何更快破案,而是如何更慢地下结论。
>慢一点,再慢一点。
>直到所有疑点都开口说话。”
写完这段话,他合上日志,起身走到窗边。城市灯火通明,车流如织。远处一栋高楼正在封顶,塔吊缓缓转动,像一座沉默的守望者。
他知道,这个世界永远不会缺少黑暗。
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在风雨中多走一步,在证据前多看一眼,在结论前多问一句,光就不会彻底熄灭。
几天后,支队迎来一批新警实习生。培训课上,陆川播放了一段模拟推演视频,主题是“如何识别被嫁祸的嫌疑人”。视频案例原型正是“张万里案”,只不过所有名字都被替换,地点模糊处理。
结束后,一名学员举手提问:“陆队,现实中真有人能设计出这么完美的陷害吗?”
陆川看了眼坐在后排的张辉,淡淡地说:“不止有,而且他们往往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坐在会议室里拍板决策。他们的武器不是刀枪,而是权力、资源和人心的弱点。所以你们要记住,破案最难的地方,从来不在现场,而在人心深处那些看不见的褶皱里。”
下课铃响,人群散去。张辉收拾笔记本准备离开,却被那个提问的学员拦住。
“张警官,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如果再来一次,您还会选择推翻最初的结论吗?哪怕这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更多的阻力?”
张辉停下动作,望着窗外渐暗的天空,许久才开口:
“会。
因为我当警察的第一天,就立过誓: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忠于内心那点不甘心。
我不怕错,只怕明知有问题却装作看不见。
如果哪天我学会了将就,那我就不再配穿这身警服。”
学员怔住了,随即郑重地点了点头。
当晚,张辉收到一条短信,号码陌生。内容只有短短一行字:
【谢谢你,让我哥的名字不再是“被杀的举报人”,而是“坚持正义的人”。】
他盯着手机看了很久,最终回复了一句:
【是他自己撑住了底线,我只是没敢放下。】
雨又下了起来,淅淅沥沥打在窗玻璃上。张辉打开抽屉,取出一份尚未归档的文件??那是王强在看守所写的悔过书复印件。纸张皱巴巴的,字迹歪斜,有些地方甚至被泪水晕开:
>“我没想杀人,也没想害谁。赵志国说,就帮我这一次,以后税务的事全搞定,还能拿五十万……我觉得划算,反正死的是个外人……
>可当我半夜开车去河边,看见张万里躺在那儿,脸上全是泥,眼睛还没闭上……我才知道,我干了件畜生才干的事。
>我不该信他。我不该贪钱。我不该以为躲过去就没事。
>现在我明白了,有些错,一辈子都还不清。”
张辉轻轻折好纸页,放进日志本夹层。他知道,这不是终点。未来还会有类似的案子,还会有更精密的伪装,还会有更隐蔽的权力游戏。
但他也相信,只要还有人在追问“为什么”,在质疑“是不是”,在坚持“再查一遍”,那么,真相就不会永远沉睡。
夜深了,办公楼渐渐安静下来。唯有档案室的灯还亮着,映照着墙上那面无人领取的锦旗,以及柜子里一本本厚重的日志。
它们静静等待着下一个故事,下一场风暴,下一位不愿将就的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