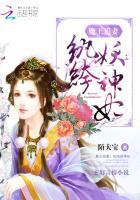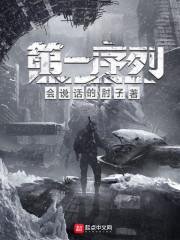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割鹿记 > 第九百八十二章 釜底先抽薪(第3页)
第九百八十二章 釜底先抽薪(第3页)
一艘无帆之船自雾中驶出,船头立一老妪,白发如雪,怀抱一口青铜匣。她不言不语,登岸后直奔归鹿观,将匣子放在林晚舟面前。
“我是阿奴。”她说,“三百年前,我曾是鹿承安的侍女。后来我跳入忘川,只为带走一段不该被遗忘的记忆。现在,我回来了。”
林晚舟颤抖着手打开铜匣。
里面没有经书,没有秘法,只有一碗干涸的墨汁,和一支用孩童指骨制成的笔。
阿奴低声说:“这是《归尘篇》的书写工具。唯有以血为墨,以身为纸,才能写下真正的终章。内容不能预先知晓,否则便失其力。执笔者必须是在光中行走一生,却始终不肯成神之人。”
林晚舟看着那支骨笔,忽然笑了。
她取来清水洗净笔身,然后割破指尖,滴血入碗。墨色瞬间复苏,泛起幽蓝光泽。
她在空白竹简上写下第一行字:
>“我从未想过要成为英雄。我只是害怕,如果我不点这盏灯,就再也没有人点了。”
笔锋落下之际,整座归鹿山谷的琉璃花simultaneous盛放,光芒不再向外扩散,而是inward收敛,汇成一点,落于她眉心。
那一瞬,她看见了全部。
看见陆昭在雪夜里折断自己的灯杖,说“光不应依附于器”;
看见鹿承安焚毁权册时眼角滑落的泪;
看见无数无名者在暗巷中点亮油灯,照亮陌生人回家的路;
还看见未来??百年之后,千年之后,仍有孩子在冬夜提灯奔跑,笑声穿透风雪。
她放下笔,轻声说:“结束了。”
阿奴摇头:“不,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
翌日,林晚舟宣布闭关,不再授课。但她要求每日清晨,有学生在第七灯亭燃一盏素灯,不题名,不祈愿,只为“提醒自己还能点燃什么”。
三年后,她病逝于归鹿书房,手中仍握着那支骨笔。临终前,她对卢疏影说:“告诉后来者,不要找下一个我。也不要找下一个陆昭。去找那些在黑暗中still伸手摸火柴的人。”
葬礼那日,天下无灯。
所有人家自觉熄灭灯火,无论油灯、蜡烛、琉璃芯,一律不燃。整整一日,大地沉于幽暗。
入夜,第一颗星升起时,不知何处传来一声轻响。
一盏灯亮了。
接着是第二盏,第三盏……很快,万家灯火陆续点燃,没有统一号令,没有仪式引导,只是人们自发地,拿出了藏在柜中的灯笼,点亮,挂起。
这一夜的光,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庆典。
它不为崇拜,不为祈福,不为驱邪,仅仅因为??有人想让别人看得见路。
而在归鹿最高处的无字碑上,光影再次流动。画中队伍依旧前行,但这一次,陆昭的身影不再站在前方引路,也不在身后守望,而是分散成了千百个模糊轮廓,融入人群之中。
他成了每一个提灯的人。
风穿过山谷,带来远方溪流上漂荡的纸灯声,??如语。
窗台上,那枚铜钱依然躺着,正面朝上,映着永不落幕的日光。
它静静地,像一颗不肯离去的心跳。
也像一句未曾说完的话:
>“你还愿意点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