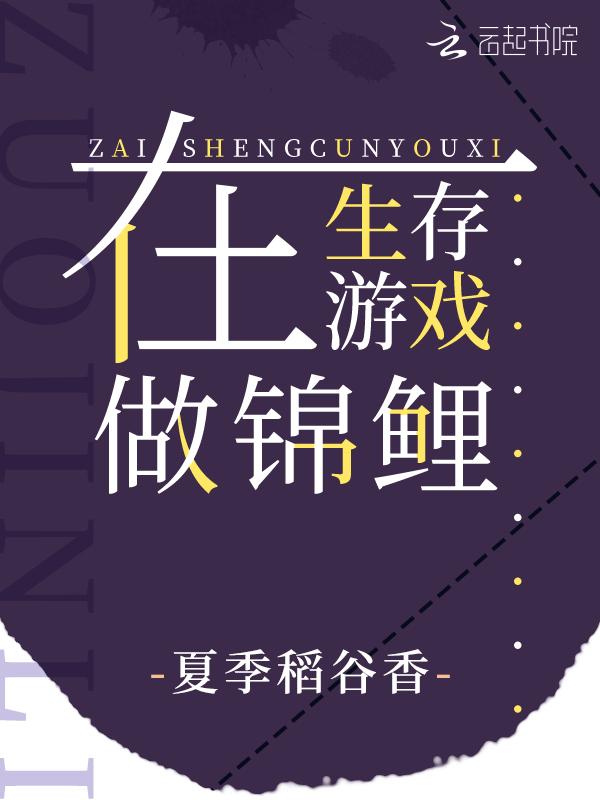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天人图谱 > 第五百零六章 灵芒遮过影(第2页)
第五百零六章 灵芒遮过影(第2页)
>“林昭:”
>“你还记得七岁那年,摔碎父亲的陶罐后躲在柴房里哭了一整夜的事吗?”
>“你一直以为他不知道。”
>“其实他知道。”
>“他捡起碎片时,在每一片上都刻了一个字,拼起来是:‘不怕,我在。’”
>“后来他把那些碎片埋在了桃树下,说等哪天你长大了,自然会懂。”
>“现在,你懂了吗?”
林昭的手剧烈颤抖起来。那字迹陌生却又熟悉,带着一种久违的温柔力道,是他父亲生前写家书时特有的风格。
“爸……”他喃喃出声,眼泪无声滑落。
他冲出屋子,奔向桃林最深处那棵最老的桃树??那是父亲亲手种下的。他跪在地上,用手疯狂挖开泥土。不多时,指尖触到一块坚硬之物。
他将其取出,拂去尘土。那是一块碎裂的陶片,边缘参差,表面布满裂纹。可在裂缝之间,竟真的刻着一个个微小的字,连起来正是:
>“不怕,我在。”
林昭抱着陶片坐在泥地上,像个孩子般嚎啕大哭。十年来,他以为自己是在替别人疗伤,却不知自己才是那个最需要被听见的人。他建静听院,种桃林,收“忏悔之花”,皆因内心深处那一声未曾回应的哭泣。
而今,父亲的沉默终于有了回音。
雨不知何时下了起来,细细密密,打湿了他的衣裳,也滋润着“和解草”的根系。雨水顺着叶片滑落,每一滴都映出不同的光影,仿佛承载着无数未说完的话。
第二天清晨,孩子们再次来到桃林。他们惊讶地发现,“和解草”竟然长高了一寸,茎干更加挺拔,四片叶子如羽翼般舒展。而在它周围,竟零星冒出七八株同样的银白幼苗,每一株都散发着微弱却坚定的光晕。
“它们是从哪儿来的?”一个男孩问。
林昭望着那些新生的植株,轻声道:“当一个人愿意说出‘我错了’,另一个人愿意说‘我听见了’,和解就开始生长。这些,是你们昨天留下的温度结出的果实。”
小女孩踮起脚尖,指着其中一株说:“那它有没有名字?总不能一直叫‘和解草’吧?”
林昭沉吟片刻,忽然想起梦中废墟里飘过的那些人脸,想起他们走过时说的每一句话。他缓缓开口:
“它不该只有一个名字。因为它属于所有人。但若非要取一个……就叫‘共语’吧??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存在。”
孩子们齐声重复:“共语……”
那一瞬,所有幼苗同时轻轻摇曳,叶片上浮现出相同的文字:
>“谢谢你们,给了我名字。”
午后,一封加急信件由山外送来。林昭拆开一看,竟是东海渔村那位小女孩寄来的。信纸上画着一幅简单的图:一只小狗趴在沙滩上,旁边坐着一个小女孩,两人中间画着一颗星星。
信中写道:
>“林爷爷:”
>“昨晚我梦见阿黄回来了。它不会说话,但它用鼻子蹭了蹭我的手,然后指了指天。”
>“我抬头看,天上有一串光点排成了‘谢谢你’三个字。”
>“我知道那是你说的。”
>“我会好好长大,也会告诉别人,道歉不是软弱,是勇敢。”
林昭将信折好,放入木匣。他忽然觉得,这个匣子不再沉重,反而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收纳着人间最真实的情感脉搏。
傍晚时分,天空骤然变色。乌云翻滚,雷声隐隐,一场罕见的暴雨即将来临。林昭正准备关门避雨,却见远处山路尽头,一个身影踉跄而来。
那人披着破旧斗篷,满脸风霜,手中拄着一根拐杖,走到桃林前才停下。他摘下兜帽,露出一张苍老却熟悉的面孔??是当年倒悬石殿考古队中那位年轻研究员。
“您还记得我吗?”他声音沙哑,“我是李彻。那晚陶片碎裂后,我就离开了队伍。这些年,我走遍西域,寻找失散的族人,重建族谱。昨天,最后一个名字补上了。”
林昭迎上前,握住他的手:“你做到了。”
李彻眼中有泪光闪动:“可我才发现,真正的传承不是名字,是承认错误的勇气。我父亲至死都没原谅我烧手稿的事……可就在前天夜里,我家祖屋的老墙上,突然浮现出一行字:‘儿,我知道你怕,没关系。’”
他哽咽难言:“原来他一直都知道,也一直在等我说那一句对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