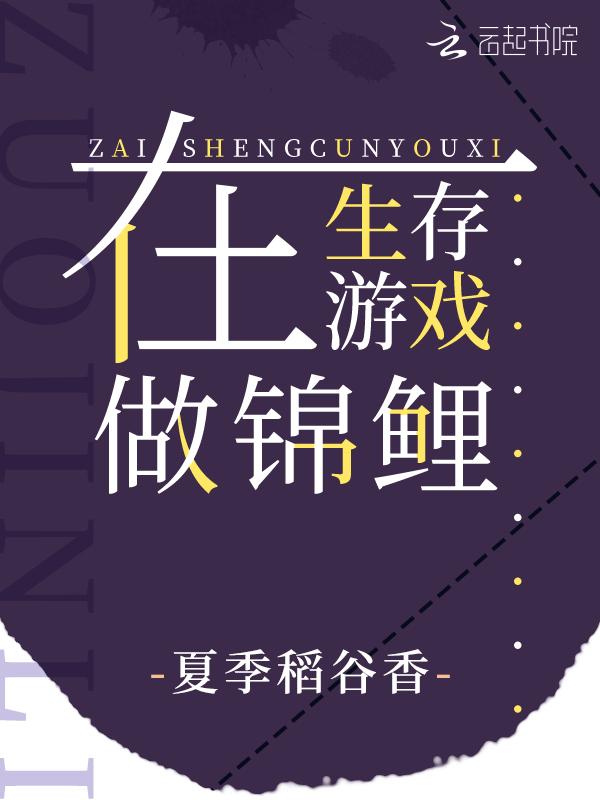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七零易孕娇娇女,馋哭绝嗣京少 > 第606章这下长记性了(第2页)
第606章这下长记性了(第2页)
“这不是普通的婴儿。”策勒脸色变了,“他是……心印网络的自然产物。”
李婉点头:“生产那天夜里,整个村庄停电。可当孩子第一声啼哭响起时,村口那棵百年古树上的铜铃,无风自动。”
三人相视无言。
几天后,联合国派来的专家团队抵达青海湖。领队是一位神经科学教授,带着最先进的脑波扫描仪和情感频谱分析设备。他们在井边架设仪器,试图捕捉所谓“共鸣现象”的物理证据。
测试持续三天,数据无数,结论却是空白。
“没有任何电磁信号超出背景值。”教授摘下眼镜,疲惫地说,“但我们录到了一件怪事??每当有人把手放在井沿上超过六分钟,他们脑电图中的α波就会同步化,且模式与全球其他参与‘倾听仪式’的人群呈现跨地域共振。”
阿岩只是淡淡一笑:“所以你们终于承认,有些连接,不能靠电线传输。”
教授沉默许久,临走前留下一句话:“我们准备在全球一百个偏远地区复制你们的模式。不是作为科研项目,而是作为人类自救计划。”
消息传开后,越来越多的孩子被送来。有的家长徒步十天赶来,只为让孩子在校门口坐一晚;有的寄来家书附带一撮故乡的土,请求埋在井旁,“让孩子的根也能听见家乡的回音”。
这一年夏天,国家教育部正式将“情感倾听课”纳入基础教育试点课程。教材首页写着一行字:
>**语言的意义,始于倾听,而非表达。**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欢迎这场变革。
某夜暴雨倾盆,学校围墙被人泼上红漆大字:“伪科学!蛊惑人心!”监控拍到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去,车牌被泥浆遮盖。次日清早,几份匿名举报材料寄至省教育厅,指控阿岩利用“封建迷信手段操控未成年人心理”,要求查封回响学校。
阿岩没有辩解,只给所有举报者写了一封公开信:
>“若您愿意,请来井边坐十分钟。不必说话,也不必相信。只要您肯停下来看一眼身边孩子的脸,就知道我们为何存在。”
信登报后第三天,一位母亲独自来到学校。她是举报人之一,儿子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药物治疗两年,仍无法控制暴躁情绪。她本欲强行带走孩子,却被眼前一幕钉在原地??
她的儿子正跪在井边,双手捧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他三岁时与父亲的合影,后来父亲因矿难去世。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他也浑然不觉,只是反复轻抚照片边缘,嘴唇微微开合,仿佛在说一句迟来了十年的“爸爸再见”。
女人蹲下身,抱住他,失声痛哭。
一周后,她撤回举报,并自愿加入家长倾听小组。
风波渐息时,聆抱着孩子来找阿岩。婴儿已满三个月,依旧不会哭闹,但每当铜铃响起,他的瞳孔便会微微扩张,像是在接收某种无形的信息流。
“我想带他去一趟昆仑山。”她说,“江老住过的木屋还在,烟囱还能冒烟。也许……那里能解开他的秘密。”
阿岩同意了。
出发那日清晨,全校师生列队送行。孩子们每人手持一支野花,插在校门口新立的石碑缝隙中。碑上刻着十三个名字??那些曾在沉默中重生的孩子,如今已在各地创办小型倾听中心。
山路崎岖,三人步行前行。越往上,空气越稀薄,可婴儿始终安睡。抵达木屋时正值黄昏,夕阳透过云层洒落雪坡,宛如金河奔涌。
聆走进屋内,在当年江慎行常坐的位置放下襁褓。她点燃炉火,煮了一壶普洱茶。
就在此刻,异变陡生。
婴儿睁开了眼。
那不是普通婴儿懵懂的目光,而是一种穿透岁月的清明。他缓缓抬起右手,指向墙壁夹层。阿岩依言摸索,从中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
盒内是一卷胶片和一张手绘图纸。
胶片经显影后,竟是三十年前的一段影像:年轻的江慎行站在实验室中,面前悬浮着一团蓝色光球。他对着镜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