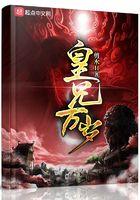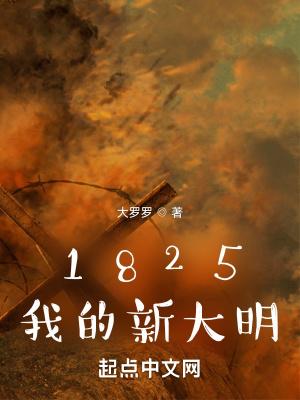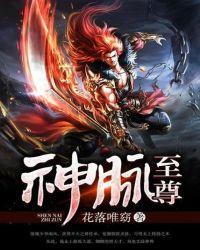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炮灰的人生2(快穿) > 2459杀猪娘子完(第2页)
2459杀猪娘子完(第2页)
他最终答应免费送所有人过河。
船行中流,月光照水如银。林知意立于船头,望着两岸苍茫大地,心中涌起前所未有的预感:这一场“万问大会”,或将改写整个王朝的认知秩序。
抵达慈恩寺时,已是秋分前夜。寺庙住持原是朝廷安插的眼线,本欲闭门拒客,却被突如其来的景象震慑??万余人自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在寺外旷野扎营露宿,篝火连成一片星海。孩子们在父母膝前练习提问,青年们互相辩论“何为正义”,老人则低声传诵那些已被遗忘的名字:陈大川、苏禾、李秀娥(三十年前因举报贪官而被沉塘的村塾女师)……
林知意走入人群,听见一个六岁男孩认真地问他母亲:“如果皇帝错了,我们也得听吗?”
母亲答:“你可以先问清楚,他错在哪里。”
男孩又问:“那要是没人敢告诉我呢?”
母亲沉默片刻,从怀里掏出一块布包,展开是一枚小小的铁笔徽章:“那就记住这个名字??林知意。她说过,当没有人回答你时,你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
那一夜,林知意彻夜未眠。她在帐篷中写下《万问宣言》,并派人快马加鞭送往各州县,同时嘱咐所有弟子:一旦大会开始,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确保至少一人活着带走全部记录。
秋分当日,朝阳初升。
慈恩寺山门前搭起一座简易高台,无顶无柱,仅设一案一椅一铃。林知意身穿粗布素衣登台,手持铁笔,身后悬挂一幅巨幅白布,上书四个大字:
**请问**
全场寂静。
她举起铜铃,轻摇一声。
“今日,我们不做讲史人,不做解惑者,不做导师。”她的声音透过扩音竹筒传遍山谷,“我们只做一件事??倾听问题。”
她指向第一排一名衣衫褴褛的老妇:“您请先问。”
老妇颤巍巍起身,声音沙哑:“我儿子十年前被抓去修皇陵,说是有功可免赋役。可他去了就没回来……官府说‘死于疫病’,可连尸首都找不到。我想问??**死去的人,有没有权利被记得?**”
话音落下,千百人低头默哀。
第二个提问者是个十五岁的少女,她是某位被贬官员之女,自幼不得入学:“我读过《女诫》《列女传》,里面都说女子应‘安守闺训’。可我也读过《种火者》,知道五百年前就有女子率众抗税。我想问??**为什么有些书教我们顺从,有些书却教我们反抗?哪一本才是真的历史?**”
第三个是一位退役老兵,曾参与北境战役:“我亲眼看见监军下令活埋降卒,可战报写的是‘大破敌军,斩获三千’。如今我每月领一份微薄抚恤,被称为‘为国尽忠的老兵’。我想问??**当国家用谎言奖励忠诚,我们还要不要效忠?**”
问题如潮水般涌来。
一个接一个,不分贵贱,不论老幼。有人问税,有人问律,有人问婚姻、科举、奴籍、边防、灾赈……每一个问题都像一把凿子,敲击着那个看似坚固实则脆弱的认知体系。
到了午时,第三十七个提问者站起,竟是当朝监察御史的独子。他神情复杂:“家父常说‘维护纲常乃士人之责’,可昨夜他偷偷塞给我一封信,让我务必来此参会。他在信中写道:‘我一生弹劾贪官无数,却从未质疑过制度本身。或许,真正的腐败不在个人,而在不允许被质疑的规则。’我想替他问一句??**当执法者也开始怀疑法律,这法律还算数吗?**”
全场哗然。
就在此时,远处尘土飞扬,一队金吾卫疾驰而来。人群顿时紧张,许多人下意识护住身边的孩子。然而为首的将领并未下令驱散,反而翻身下马,摘去头盔,露出一张饱经风霜的脸。
他是前任兵部尚书之弟,曾在西南镇压民变,后因目睹真相而辞官归隐。此刻,他走到台前,单膝跪地,从怀中取出一份泛黄军报副本:
“我在军中三十年,亲手焚烧过十七份真实战报。今天,我要补上一个问题??**当胜利建立在尸体数量的伪造之上,这场战争,究竟赢了什么?**”
他将文件放在台上,转身离去,背影萧索而坚定。
林知意含泪宣布:“这些问题,我们将整理成册,命名为《万问录》。不求立刻答复,只求不让它们消失。”
傍晚时分,天空忽降细雨。雨水打湿了白布上的“请问”二字,墨迹缓缓流淌,仿佛泪水划过脸庞。然而人群依旧伫立不动,甚至有人开始齐声朗诵《种火者》终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