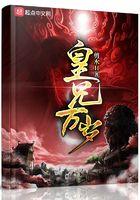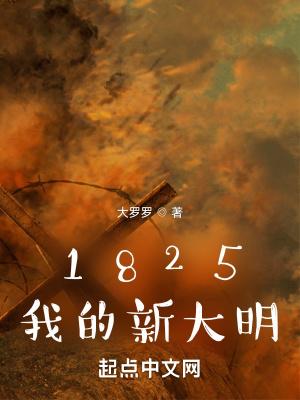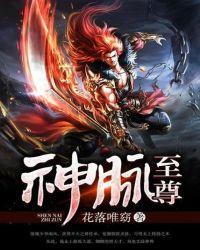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娘子,别这样! > 第569章 当街弑君五千(第2页)
第569章 当街弑君五千(第2页)
宁平冷笑一声,抓起墙角铁铲,吹熄灯火,悄然退入后山密道。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守在这里了。他必须动起来,像林远昭一样,成为那个把火种送往四方的人。
***
三日后,河西走廊,沙州驿站。
一名老驿卒正在清扫庭院,忽见门外倒着一人,浑身是血,怀中死死护着一本破旧册子。驿卒急忙救人,待其苏醒,才发现竟是林远昭。
老人虚弱地睁开眼,第一句话便是:“带我去莫高窟。”
驿卒犹豫:“那边……已被思正台盯上了。前日抓走了三个抄经僧。”
林远昭艰难坐起,从怀中掏出半页烧焦的纸片,上面依稀可见几个字:“……昆仑墟……归门启,则忆海涌……”
“这不是故事,”他声音沙哑,“这是钥匙。只要有人读懂它,就能唤醒沉睡的记忆之源。”
驿卒看着他眼中燃烧的火焰,终于点头。
当夜,两人驾一辆运粮车混出城外。行至中途,忽闻马蹄声疾驰而来。数十骑黑甲骑兵包围车队,为首者冷声道:“奉思正台令,查验违禁文书!”
林远昭迅速将残页塞入口中吞下,随即抓起一根木棍,撞开车厢暗格,放出藏在夹层中的微型刻印机??这是柳芸临被捕前交给他的最后一件工具。
“走!”他对驿卒吼道,“去敦煌!告诉玄觉,昆仑之门要开了!”
话音未落,一支箭矢贯穿其肩。老人踉跄跌倒,却仍挣扎着在地上用血写下最后一句:
**“记得即是存在。”**
骑兵冲入车厢搜查,只找到一堆空白桑皮纸。他们怒而纵火焚车,扬长而去。
然而,就在火焰升腾之际,那些看似无字的纸张竟在高温中显现出密密麻麻的文字??正是《共生识论》的核心篇章。风卷灰烬四散,如蝶飞向远方。
***
敦煌莫高窟,第17窟(藏经洞)。
画僧玄觉盘坐于地,面前摆着青铜匣。小满跪在一旁,双手合十。老僧缓缓打开匣子,取出玉佩与手稿,凝视良久,忽然泪下。
“原来如此……”他低语,“他们一直以为记忆是结果,殊不知,记忆才是起点。”
他起身走向石壁,以指为笔,在岩面上缓缓刻画。随着线条延伸,一幅巨大壁画逐渐成形:中央是一口深井,井边站着无数人,手牵手围成圆圈;井中升起一条光河,直通天际;而在河尽头,赫然是昆仑雪山之巅,一座巨碑巍然耸立,碑前跪着九位身影,皆背对观者,长发飞扬。
玄觉转身对小满道:“明日午时,我会召集三百画工,在此窟内外同时绘制此图。每一笔,都是一次铭记;每一色,都是一声呼唤。”
他又取出一只陶罐,倒出细粉,洒于地面。粉末遇空气竟自行排列成字:
**“昆仑墟,西出玉门三百里,雪线之上,孤峰独峙。碑在山腹,门由心启。”**
小满瞪大双眼,急忙记录。
玄觉叹息:“三十年前,我曾随师至此。那时碑尚未封,尚能听见里面传来诵经声。后来朝廷派人用铅汞封山,说是‘镇压邪祟’。其实……他们怕的是百姓记得太多。”
他望向窗外月色,喃喃道:“宁平、林远昭、柳芸、苏婉儿……你们点燃了火,现在,轮到我们传递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