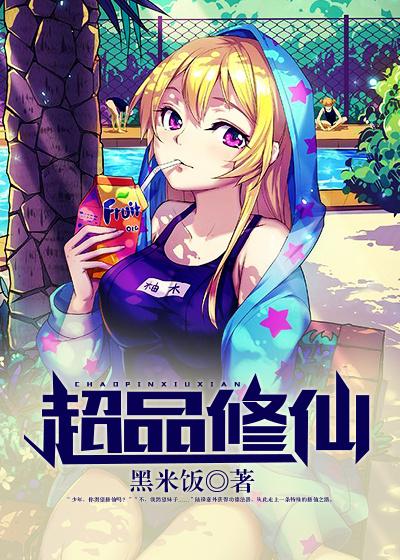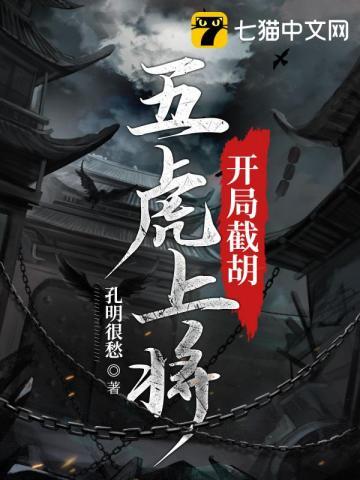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内娱顶流:从跑男出道 > 第三百九十五章 筷手整改新同桌7 5k(第1页)
第三百九十五章 筷手整改新同桌7 5k(第1页)
……
……
“老板,新的分成合约已经谈妥了,您的个人分成比例从原先的10%提升到了15%,公司那边也最终点头同意了。”
电话那头,传来许伟的声音。
“对了,还有您之前特别关心的。。。
四月的陇西,梨花落尽,新叶初生。晨光透过排练厅斑驳的玻璃窗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影,像无数未说完的话。张松文坐在角落的老木椅上,手里捏着一支铅笔,正一页页翻看那本护工寄来的日记。纸张泛黄,字迹潦草,却一笔一划都透着沉重的温度。
“今天,4号床阿珍又撕了她的病历卡。她说:‘我不是疯子,我是被丢下的。’她记得自己是广西梧州人,1978年考上师范,可还没去报到,家里就出了事??父亲被打成右派,母亲上吊,弟弟送人后音讯全无。她一个人撑了三年,最后精神崩溃。现在她每天写信,写给一个不存在的地址:梧州塘尾街17号。她说,只要信还在写,家就还没塌。”
张松文闭上眼,喉头滚动。他想起林晓梅姐姐捧着布片痛哭的模样,想起祁连山风雪中飘起的三百朵纸梅。有些记忆不是疾病,而是太深的爱无法安放。
“我们得去。”他睁开眼,对刚进门的马小梅说,“去那个精神病院。不止是为了演出,是去听他们说话??真正地听。”
马小梅点头,眼神坚定:“我已经联系了广西民政和卫生部门,对方愿意配合。但有个条件:不能拍摄患者正面,不能公开姓名,所有素材需经伦理审查。”
“可以。”张松文写下一行字:“《重逢?无声者》。”
三天后,剧组启程南下。
火车穿过秦岭、越过长江,窗外景色由荒原渐变为葱郁丘陵。途中,王杰调试着最新版的“声音寻人”设备??这次加入了情绪识别模块,能根据语音波动判断讲述者的心理状态。“如果一个人讲完故事后心跳加快、声线微颤,说明那段记忆仍在刺痛他。”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这痛被看见。”
抵达梧州时正值清明雨季。城市笼罩在薄雾中,街道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漫着艾草与香火的气息。精神病院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红砖墙爬满藤蔓,铁门锈迹斑斑。院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女医生,姓陈,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轻而有力。
“你们不是第一批来采风的文艺团体。”她领着众人穿过长廊,“但大多拍点镜头就走了。没人愿意花时间坐下来,听他们讲完一句话。”
走廊两侧病房门半开,偶尔传来低语或笑声。有的病人安静地看着窗外,有的反复整理床单,动作机械却专注。陈医生停下脚步,指着一间房:“阿珍住这儿。她情况稳定,只是拒绝承认现实。我们没告诉她弟弟死了,也没说她家老屋早拆了。有时候,谎言比真相更温柔。”
张松文轻轻推开门。
女人坐在床边,背对着门口,正在叠纸。她头发花白,手指枯瘦,但动作极有条理。每叠好一只纸鹤,就放进一个玻璃罐里。罐子已经快满了。
“今天写信了吗?”马小梅蹲下身,声音柔和。
阿珍转过头,眼神清明:“写了。我说今年清明我替他烧了纸,坟前放了酒。他还爱喝米酒吗?”
没人接话。静怡悄悄红了眼眶。
“您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张松文问。
她笑了,从枕头下抽出一张照片??黑白的,一个小男孩扎着头巾,站在荔枝树下啃甘蔗。“这是他七岁那年拍的。后来……后来我就再没见过他。”她顿了顿,“但我每年都给他折纸鹤。一百只,代表一年。等攒够五十罐,我就去找他。”
张松文忽然起身,走出房间。
半小时后,他带着一台老式录音机回来,还有一卷空白磁带。
“我想请您录一段话。”他对阿珍说,“不是写信,是直接对他说话。我们会想办法,把声音送到他知道的地方。”
阿珍怔住,嘴唇微微颤抖。良久,她点点头。
录音开始时,雨正敲打着窗户。
“阿弟啊……”她的声音沙哑,却异常清晰,“姐姐在这里,还好。药吃得下,饭也热乎。你别担心。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公安局说档案丢了,可我不信。你是塘尾街出来的崽,骨头硬,命也硬。你现在在哪?结婚了吗?孩子叫什么名字?要是听见这段话,就回个信吧。不用寄到医院,寄到老屋门口那棵龙眼树就行??我知道它还在,根没断。”
她说完,轻轻抚摸录音机,像摸孩子的头。
当天晚上,剧组召开紧急会议。顾顶已通过公安系统协查,确认阿珍弟弟李建国确于1979年被送往贵州某农场安置,1985年登记死亡,但无尸检报告,家属未签字。“很可能是误报。”他说,“那时候信息闭塞,一人走失,全家销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