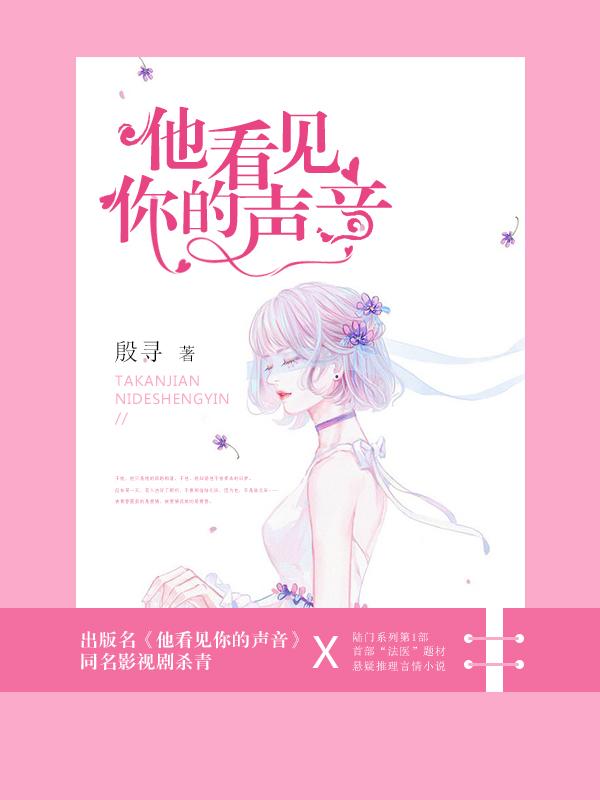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美食之灵 > 第28章 群策群力(第1页)
第28章 群策群力(第1页)
“零拒绝!”
在第一天美食马拉松结束后,第一时间找到戴兰和秦琅的杜子岩微微昂起头来,骄傲地宣布自己的战绩。
“一整天时间,我不仅完成所有食客的需求,更是获得了足足两张‘拒绝卡’!”
。。。
砂锅置于炉上,火苗自底部悄然舔舐。秦琅将那几粒五香豆倒入清水中浸泡,动作轻缓,仿佛怕惊扰了沉睡在豆壳之中的记忆。水波微漾,黑色的豆粒缓缓舒展,像是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他取出父亲留下的老式铜秤,逐一称量八角、桂皮、甘草、丁香与花椒??每一种香料都需精确到克,误差不可超过半钱。
这不是普通的复刻。
这是对一段人生、一场爱情的临摹。
老人坐在角落的木椅上,未脱下外套,也未曾坐下太久便已显出疲态。但他始终睁着眼,目光如钉子般钉在秦琅的背影上。他的手指轻轻摩挲着胸前那枚铜质徽章,上面刻着一个模糊的篆体“味”字,边缘已被岁月磨得发亮。
秦琅知道,这枚徽章不属于任何公开组织,也不是烹饪协会的认证标志。它是“守味人”的信物??传说中那些游走于城市缝隙之间,守护即将消亡之味的隐士才配拥有。而眼前这位老人,或许正是最后一位活着的传承者。
水沸了。
他将泡好的豆子捞出,投入滚水中焯去涩味,再换冷水冲洗三遍,确保每一粒都干净通透。接着,香料入锅干焙,火候极小,仅以余温唤醒其内在芬芳。八角裂开细缝,桂皮卷曲起边,丁香释放出近乎药性的苦香……整个厨房弥漫着一种古老而庄严的气息,像寺庙清晨焚起的第一炷香。
“你用的是江西产的八角?”老人忽然开口,声音低哑却清晰。
秦琅回头,点头:“三年陈,阳光晒足一百八十日,水分控制在12%以下。”
老人微微颔首:“她也是这么挑的。”
秦琅没说话,继续操作。他知道,真正的五香豆,关键不在香料本身,而在“浸”与“煨”的节奏。传统做法讲究“三浸三煨”,即豆子要经历三次冷水浸泡与三次慢火煨煮,每一次间隔十二小时,让味道层层渗入核心。但如今谁还有这般耐心?机器量产的五香豆往往一锅炖到底,香气浮于表面,内里空洞无魂。
可今晚,他决定走那条最笨的路。
第一轮煨煮开始。砂锅加盖,文火慢炖,豆身逐渐膨胀却不破皮。秦琅坐在灶前,手中握着一支竹制计时签,那是母亲生前用来记录火候的小工具。每过一小时,他便轻轻掀盖,用筷子轻拨豆粒,观察其软硬程度,并调整火力。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窗外月移星转,夜风拂动檐角铜铃,发出细微叮当声。蛋宝和辣辣早已醒来,蜷缩在烤箱余温旁,静静望着主人忙碌的身影。它们不再嬉闹,仿佛也感知到了这一晚的不同寻常。
第二轮浸泡时,秦琅加入了微量海盐与一小片陈年橘皮。这是他在某本民国食谱残页上看到的秘法??橘皮不仅能去腥增香,还能让豆仁口感更绵密。他记得母亲曾说过:“好味道,从来不靠一味压倒另一味,而是让所有滋味学会共处。”
第三轮煨煮最为关键。
他将前两轮的汤汁滤净,重新调入新炒过的香料,加入半勺由鸡骨熬成的老卤底。此时火候必须精准到秒:太大则豆烂汤浑,太小则味不入心。他闭眼倾听锅内气泡破裂的声音,凭借二十年灶台经验判断内部状态。
就在最后一次关火前,他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他脱下手套,用指尖轻轻捏碎一颗已熟透的五香豆,将其碾成泥状,混入汤汁中搅拌。这个动作叫“引魂”,是父亲酒后醉语中提过的土法??用一颗已化的豆子作为“引子”,带动整锅豆群共鸣,使味道更加醇厚统一。
老人眼中闪过一丝震动。
“你也懂‘引魂’?”他喃喃道。
秦琅只是轻轻说:“我娘做过一次,为了哄我开心。她说,有些味道,光靠手做不出来,得用心喂进去。”
话音落下,满室寂静。
待最后一锅五香豆出锅,已是凌晨三点十七分。黑亮饱满的豆粒静静卧在青瓷碗中,表面泛着油润光泽,香气并不张扬,却如丝线般缠绕鼻尖,久久不散。秦琅端着碗走到老人面前,轻轻放下。
老人没有立刻动筷。
他盯着那碗豆,许久,才缓缓伸出颤抖的手,夹起一粒送入口中。
牙齿轻咬,外壳微裂,紧接着是绵密沙糯的豆仁在舌尖化开,五种香料的味道依次浮现:先是八角的甜暖,继而桂皮的辛醇,甘草回甘垫底,丁香提神点睛,花椒则在喉间留下一抹温柔麻意。诸味交融,竟形成一种难以言喻的平静感,仿佛时光倒流,某个秋日午后,阳光洒进小院,妻子正坐在藤椅边剥豆哼歌……
老人的眼泪,无声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