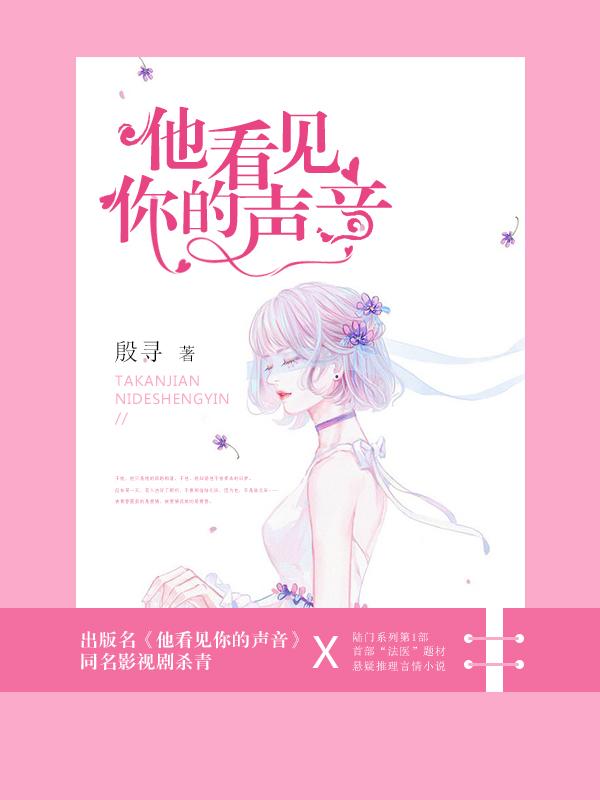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军途:从一封征兵信邮寄开始 > 第三百五十四章 盗取团旗谋划双线(第1页)
第三百五十四章 盗取团旗谋划双线(第1页)
战俘营,是演习期间专门用来看守战损敌军的地方。
一般情况下。
各单位安置关战俘的区域,都会选在偏远,或者远离己方营区的区域,目的也是为了避免被敌军找到机会反扑。
但战训就不一样了。。。。
清晨六点十七分,昆仑山主控站的空气里弥漫着低温金属与电子元件运转时特有的微腥气味。林远站在环形监控墙前,目光扫过三百二十七个实时画面??从漠河北极村的雪原哨塔,到南沙永暑礁上空飘摇的信号旗;从四川大凉山深处一座废弃邮电所内仍在滴答作响的老式电报机,到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某极地科考站自动上传的一段摩尔斯编码音频。
一切正常。
“地脉链”稳定运行,节点之间数据流动如血液在血管中静静奔涌。那些曾被深埋、遗忘、误读的信息碎片,如今正通过加密信道重新聚合,形成一张横跨时空的认知网络。它不再只是军事意义上的战略备份系统,而成了某种更复杂的东西:一个由记忆驱动的文明免疫机制。
林远端起桌上早已凉透的茶杯,抿了一口。茶叶沉底,像年久失修的电路板上凝固的焊点。他忽然想起昨夜做的梦??不是关于战场,也不是任务失败的惊醒,而是童年某个夏天傍晚,父亲坐在院中竹椅上看报纸,母亲在厨房炒菜,锅铲碰撞声清脆入耳。风穿过巷口,吹动晾衣绳上的蓝布衫,也带来远处广播站每日准时播放的《东方红》前奏曲。
就在那首歌响起的瞬间,父亲抬起了头,望向院子角落那口老井,低声说了句什么。林远听不清,可他知道,那是他人生第一次感受到“不对劲”的时刻。
后来他才明白,那一眼,是交接。
“林顾问。”身后传来脚步声,是殷蓉。她换了身常服,肩上披着件旧军大衣,手里抱着一台便携终端,“刚收到武威工程队传回的最后一份分析报告。”
林远转身接过设备,屏幕亮起,显示的是XN-719电台芯片恢复出的完整日志。除已知的地脉校准参数外,还有一段隐藏分区被成功解密:
>【记录编号:GL-880412】
>时间:1988年4月12日23:17
>地点:柴达木临时指挥舱(代号“青萍-B”)
>记录人:周德海
>
>今日完成最后一次节点同步测试。TQ-312原型机确认可承受EMP冲击及地下三十米封闭环境长期待机。备用机已按预案埋设于武威西山区域,坐标加密存入独立存储模块。
>
>老林说,我们这代人可能等不到火种点燃的那天。但只要有人愿意挖,就说明光还没灭。
>
>我把儿子的照片夹进了操作手册。如果将来谁找到它,请告诉他:爸爸没逃,也没忘。
>
>另:李承业昨天深夜独自进入主控室三十七分钟。未触发警报,但监控录像出现十二秒空白。我调阅了能源波动曲线,期间有短暂高频共振现象,频段接近“地脉唤醒阈值”。
>
>我不敢上报。怕错判同志,更怕……真的判对了。
林远的手指僵在屏幕上。
“周德海怀疑李承业叛变,早在1988年。”殷蓉声音压得很低,“但他选择了沉默,只把证据藏进一台即将封存的机器里。”
“因为他知道,一旦揭发,整个‘灰线’就会陷入内部清洗。”林远缓缓闭眼,“而那时,外部压力已经太大,经不起一丝裂痕。”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只有终端散热风扇发出轻微嗡鸣。
“也就是说,”殷蓉轻声道,“李承业的背叛,并非突发行为,而是一场长达数年的渗透准备。他在系统内部制造漏洞、复制密钥、甚至可能提前布置了‘灰影协议’的种子程序……”
“所以他能在关键时刻切断‘信使之网’,却不彻底摧毁它。”林远睁开眼,“因为他需要它活着??作为诱饵,也作为后门。”
两人对视片刻,无需多言,都明白了接下来的问题有多危险。
“现在这些自发加入的‘见证者’,会不会已经被反向渗透?那些提交线索的人里,有没有人其实是……他们派来的?”
林远没有立刻回答。他打开“根脉”权限审计日志,筛选过去七十二小时内新增访问请求。两万三千余名民间用户提供信息,其中一万八千余人已完成身份交叉验证,来自公安、退役档案、邮政系统等可信数据库。但仍有五百余人无法溯源,仅凭手写信或匿名上传方式参与。
最可疑的是三个IP地址,均位于境外数据中心,却使用极为精准的术语描述“青萍行动”内部流程,甚至提到了从未公开过的“钟楼谐振实验”。
“伪装得太好了。”殷蓉皱眉,“普通人不可能知道这些细节。”
“但也可能是真正的幸存者。”林远摇头,“三十年前,有多少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触过核心信息?教师培训营里的技术讲师、军工医院的心理评估员、边防电台的临时调度员……太多灰色岗位游离在正式编制之外。”
他顿了顿,忽然问:“扎西呢?他那边有什么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