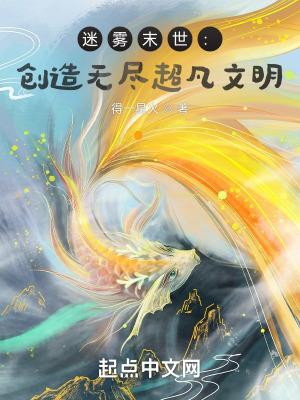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云山雪 > 为谁流下潇湘去其八(第3页)
为谁流下潇湘去其八(第3页)
铜镜宽阔清晰,钟滟擦着发尾,照得十分满意。这桌子虽无初昀阁里二师兄为她打得那张繁复精巧,满是可藏香囊发带的巧格抽屉,但却清爽大气,很是实用。
奇怪,夕照居里素来简朴,何时添了这张镜桌?
她的思绪乱飞,骤然被肩头痛楚打断——不知何时林维清已站在了她身后,正将她肩头沾湿的绷带剪下,要为她换药。
“我自己来就好。”她惊得一跳,她昏睡脱力时也就罢了,如今人好好的,怎么还能劳动师父。
林维清却一把按住她的肩头,将她塞回座上,语气有些严厉:“怎么湿成这样,你几岁了,不知道自己有伤,还泡在水里?”
左右已经命不久矣,这点小伤算什么……
钟滟很坦然,嘴上却不敢犟:“是,徒儿知错。”
整日里就会卖乖,林维清叹了口气,手上动作惩罚性地加重,擦干水渍,厚厚地抹了层膏药,紧紧地束上了干净布带。
钟滟疼得龇牙咧嘴,眼角都带了分泪光。她委委屈屈地穿好衣衫,快退几步缩到房内一角,警惕地看向林维清,决定先下手为强:“师父的药喝了吗?!”
林维清眉梢一跳,看着小徒弟的脸色立刻由阴转晴,蹦蹦跳跳地从食盒里取了药碗,又得意洋洋地端到他面前,差点被气笑了,接过一饮而尽。
放下药碗,林维清接过小徒弟殷勤递来的温水,认真解释道:“沉宥并未入为师门下,只你韩师伯如今事忙,不过容他在此暂住几日。待山中客人走后,为师自会遣他回青钢峰。”
钟滟一愣。
可是过不了几天,待段铭辞行时,她也要跟着“走”了。
到时偌大的玄晖峰,不是只剩下师父一人。
见小徒弟只一味发呆,林维清面色也有些不自然,低声道:“往后为师再不收别的弟子,玄晖峰……只为师与你二人,可好?”
钟滟却有些焦急,根本未听清那句几乎混在窗外风声中的轻语,病急乱投医道:“师父,要不您还是将林师弟留下来吧?”
林维清怔了怔,眸色似深海中震颤的烛影,明灭一霎。
钟滟有一瞬恍惚,待定睛再望,眼前人的面色却已恢复如常,如云山每夜冰雪凝霜的月光一般,望之生静。
她的思绪流转,忽而又生出心思,小心翼翼道:“师父……其实二师兄,在神焰教过得很不好。”
长睫微垂,林维清侧头望向窗外,并不答话。
钟滟仔细观察了一阵,见他似是对这话题并无抵触,才缓缓道:“二师兄被苏潋骗入神焰教后,虽想借机策反苏潋手下的六堂部众,可惜不幸事败,被苏潋投入了万蛊池,中了生灭蛊。”
林维清回过神来,眉间一蹙,若有所思地重复了遍:“生灭蛊?”
“是,那蛊好生厉害,将二师兄折磨得……”钟滟喉间微哽,几乎不敢回想上次见到沉樾时,他那狼狈憔悴的模样。
见林维清眉间更紧,面色深沉,钟滟心头一紧,忙继续道:“好在后来二师兄身上的生灭蛊总算解了,只可惜生灭蛊王在认主羽化时,被苏潋杀了……苏潋说,吸收了生灭蛊的精华,二师兄至少能得常人苦修五十载的功力……是真是假,我也不敢肯定。”
默然许久,林维清忽然开口问:“那日,你可曾探过樾儿的脉象?”
钟滟一愣,摇了摇头。
那日事发仓促,她甚至没来得及探问清楚,也不知苏潋之后会如何安置二师兄。
绞了绞手指,钟滟小心翼翼地试探道:“二师兄毕竟已踏入五重之境,就算此后功力难再精进,若他愿意回来,是不是在云山也还能有一峰之地?如今渡厄峰正好无人看守,不如……”
林维清却什么都没有再说,只转身向外间快速行去。
看他的模样也不似生气,钟滟不解,匆忙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