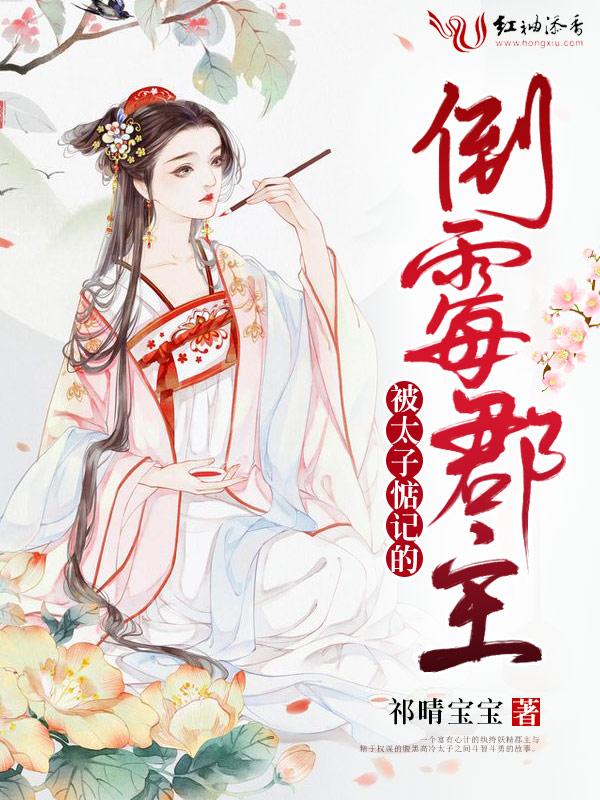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出宫前夜,疯批帝王后悔了 > 第472章 天生的朋友(第1页)
第472章 天生的朋友(第1页)
晚余听闻祁让要送她礼物,眼睛瞬间亮起:“殿下真的要送我礼物吗,我长这么大,除了阿娘,还从来没有人送过我礼物。”
她很开心,没有因着从未收到别人的礼物而沮丧难过,有的只是对即将收到礼物的憧憬和期待。
祁让的眼眶莫名有些发胀。
原来小时候的晚余是这样纯真善良,开朗乐观。
尽管生活并不如意,只能被禁锢在这方小天地和阿娘相依为命,她却毫不在意,也不会自怨自艾,一点小小的善意都能让她开心不已,普普通通的日子。。。。。。
夜风穿帐,烛火摇曳。晚余搁下笔,指尖微凉。她凝视着那行墨迹未干的文字,仿佛看见母亲在草原上教孩童识字的身影,父亲于朝堂之上怒斥奸佞的背影,还有祁让临终前握着她手时那一声低语:“别停下。”
她闭目深吸一口气,将纸卷封入竹筒,交予阿芜:“明日一早,送往长安国子监,刊印传世。”
阿芜接过,欲言又止:“先生……您真要亲自回京?可汗已允诺退兵,边患暂平,不如暂留玉门,整顿军民,待朝廷派使迎您?”
“我不回去,谁来守住这份和平?”晚余起身披衣,步出帐外。月光如练,洒在盟誓高台之上,那方刻有汉藏双语的石碑尚新,字字如刀凿心。“李德全虽倒,但宫中暗流未息。若新政无主,佑安帝孤木难支。我若贪安边陲,便是辜负所有为‘真’而死之人。”
阿芜默然良久,终轻声道:“可您知道,一旦踏入紫宸殿,便再无退路。权柄之争,比战场更噬人。”
“我知道。”晚余望着北方星河,“可正因为知道,才不能逃。”
次日黎明,队伍再度启程。
霍昭率三百玄甲残部断后,盔甲染血未洗,却已不见昔日戾气。他策马立于戈壁边缘,回望吐蕃营地方向,眼中复杂难言。一名曾随他征战的老卒低声问:“将军,我们真的能回去吗?”
霍昭沉默片刻,抬手抚过脸上疤痕,缓缓道:“只要她还在前面走,我们就还能找得到路。”
行至第七日,途经梅岭旧址。
此处原是晚余讲学之地,三年前遭官府焚毁,如今断壁残垣间竟已有书声琅琅。一群少年正围坐废墟之中,捧读《金殿录》残卷,见游骑到来,齐刷刷起身跪拜。
“先生!”一名稚龄童子奔出人群,双手奉上一本破旧册子,“这是我们抄的《辨伪录》,共七十三页,缺了最后三页……但我们记得您说过的话:‘史可篡,心不可欺。’”
晚余下马,接过那本沾满尘土的抄本,指尖轻颤。她蹲下身,抚摸孩子的头:“你们不怕吗?抄这种书,会被抓去砍头的。”
“怕。”孩子点头,“可更怕长大后变成说谎的人。”
众人动容。
阿芜含泪笑道:“先生,您看,光已经扎下根了。”
晚余站起身,面向众学子朗声道:“今日我许你们一个承诺??待我归朝,必奏请重开书院,设‘明经科’取士,不论出身,唯才是举!我要让天下读书人,不再只为功名折腰,而是为真理发声!”
欢呼声震彻山谷。
当晚宿营山脚,晚余召霍九渊、程砚、阿芜议事。
“京城局势愈发凶险。”程砚摊开密报,“昨夜禁军换防,原属李党之右卫突然接管皇城四门,左谏议大夫暴毙狱中,死状可疑。另有消息,皇太弟霍衍已在府中私聚旧部,疑似图谋逼宫。”
霍九渊怒拍案几:“这畜生!先帝待他不薄,竟敢觊觎大宝!”
“他是棋子。”晚余冷静道,“真正幕后之人,恐怕是那位一直隐于深宫的太后。”
三人皆是一震。
阿芜低声道:“您是说……当年毒杀先皇后、扶持幼帝登基的那位?”
“正是。”晚余眸光如刃,“她掌宫三十年,六任阁臣皆出其门下。李德全是她的爪牙,而霍衍,不过是她用来遮掩野心的幌子。如今新政动摇她的根基,她岂会坐视?”
程砚皱眉:“可若她掌控内廷,又有禁军支持,我们千里奔赴,只怕未入城门便遭伏击。”
“所以不能硬闯。”晚余取出星盘,对照舆图,“我们改道走子午谷,绕开潼关防线,由南面潜入终南山。那里有我昔年布下的暗线,可联络禁军中忠于先帝的‘赤心营’旧部。只要里应外合,便可直逼紫宸殿。”
霍九渊沉吟:“但子午谷险峻异常,雨季将至,山洪频发,稍有不慎便会全军覆没。”
“比起死于阴谋,我宁愿死于天意。”晚余起身,目光扫过三人,“此行九死一生,愿随者自报名号。”
翌晨,点将完毕。
三百轻骑精锐随行,其余伤员留驻梅岭,由副将统管。霍昭主动请缨断后防追兵,霍九渊则率前锋探路。阿芜携《金殿录》原本及各地民情奏报同行,以备朝议之用。
临行前,晚余独自登上梅岭最高处,焚香祭拜亡师故友。
青烟袅袅升腾,她低声念道:“老师,学生回来了。这一次,我不求活命,只求能让你们的名字,堂堂正正写进史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