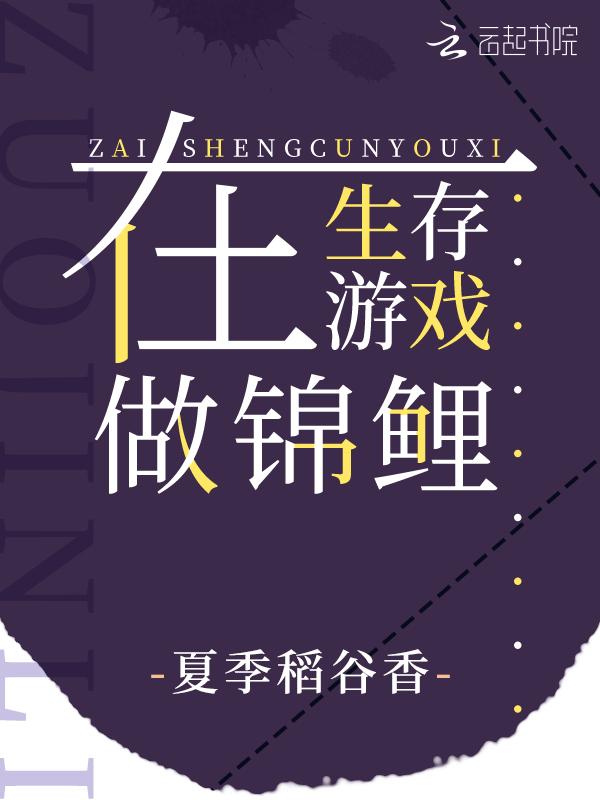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儒道玄途 > 第二百七十六章 郑凌峰归来(第1页)
第二百七十六章 郑凌峰归来(第1页)
东南海域,浪涛翻涌,闽帆军的舰船如游龙般穿梭巡航。
他们以战养战,早已将东瀛与各国建立的商贸站点连根拔起,败逃的东瀛出征军被彻底打散,再也无力集结对外出战。
“军长,远处发现东瀛舰船!”一。。。
夜雨如织,落于南荒书院的青瓦之上,滴滴答答,似万古未尽之语。守碑少年自梦中惊醒,手心犹觉石板粗粝,指甲缝里仿佛还嵌着刻字时崩裂的碎屑。他坐起身,窗外风雨正急,屋角油灯将熄未熄,光影摇曳间,那支竹笔静静躺在枕畔,两个小字“慎言”在昏黄中泛出幽光。
他不敢触碰,却又无法移开目光。
“我在你们每个人的笔尖。”??那句话不是写出来的,是直接长进他梦里的,像一根刺,扎进了魂魄深处。他忽然想起十年前那个雪夜,老者焚简成殿,信狱虚影现世,万人跪拜,天地同悲。那时他还小,只知跟着哭,却不知为何而泣。如今才懂,那是千万人被压抑的言语第一次集体破土而出的声音。
他披衣下床,赤脚踩在冰凉的地砖上,走到院中。碑前香炉残烬未灭,雨水打在上面,腾起一缕缕白烟,如同亡魂低语。他抬头望天,乌云翻涌,偶有电光撕裂苍穹,照亮碑面新显的字迹:
>“路未尽,行者不孤。”
>“我在你们每个人的笔尖。”
字迹非金非石,似由无数细小的文字堆叠而成,近看竟是《人间录》中的段落:某村妇控诉征税吏强抢嫁妆、某书生因批注《孟子》被革除功名、某匠人记述官府强征民工修陵致家破人亡……这些早已录入人间录的冤屈,此刻竟自行重组,化作箴言,浮于碑上。
少年浑身颤抖,忽然明白??这不是纪念,这是回应。
他转身奔回房中,取来墨砚与宣纸,欲将所见记录。可笔尖刚触纸面,墨汁竟逆流而上,渗入笔杆,整支狼毫瞬间转为灰白,继而寸寸断裂,如枯骨崩解。他怔住,低头再看那支竹笔,它微微震动,仿佛有生命般滚落桌沿,直直指向门外。
他知道,该走了。
三日后,江南驿道上传出一则奇闻:一名白衣少年手持无字竹笔,沿路书写。他不写于纸,而是在桥栏、墙垣、树皮上划痕,所过之处,凡曾蒙冤之地,草木皆生异象??枯枝抽芽,败叶返青,井水沸腾,石碑自动浮现旧案始末。百姓传言,此人乃“录魂使”,奉信狱之命巡游天下,唤醒沉睡真相。
与此同时,京师皇宫内,皇帝彻夜难眠。
自设立“鸣冤鼓”以来,每日击鼓者络绎不绝,御前奏对已成常例。起初尚能一一裁决,可随着民间议政之风日盛,《人间录》抄本遍布乡野,连牧童放牛时也背诵“民权十二条”,朝堂威仪渐失。更有甚者,去年冬,一名八岁童子因父亲被豪强逼死,竟携《人间录》残页闯宫,当众质问宰相:“您说‘刑不上大夫’,可我家三代良民,何罪之有?”满殿文武哑口无言,皇帝亦只能含泪赦免其家赋役十年。
如今,连宫中太监也开始私下传抄《新春秋》,内务府账册屡次被人用朱笔批注“此处虚报三千两”,吓得管事连夜烧毁旧档。
皇帝立于御花园高台,望着远处百姓聚集的“言巷”??那是朝廷被迫划出的公共议事区,每日清晨开放,允许平民辩论政事。此刻人群喧沸,一名盲眼老妪正拄杖登台,声嘶力竭控诉地方官隐瞒瘟疫、延误救治之事。她身后挂着一幅图卷,绘的是数百具裹尸草席排列如田垄,题曰《癸卯年春疫实录》。
“父皇,何必纵容此等乱象?”太子悄然走近,眉宇凝霜,“儒道讲秩序,岂容庶民妄议朝纲?苏蘅之变已乱天下十年,若再任其蔓延,恐有倾覆之危。”
皇帝缓缓摇头:“你以为是她在乱天下?不,是天下本就不平,她只是让沉默的人开了口。”
“可人心易煽,真假难辨!前日有狂徒伪造《人间录》条目,诬陷礼部尚书贪墨军饷,险些激起兵变!今日又有术士自称‘笔灵附体’,蛊惑乡民掘地寻玉,说是‘第七玉重生’!这哪还是治国?分明是群魔乱舞!”
皇帝闭目良久,忽问:“你还记得你母后临终前说的话吗?”
太子一震。
“她说:‘我这一生读尽诗书,却从未敢问一句??为什么女子不能科举?’”皇帝睁开眼,目光如刃,“我们守的是庙堂的安稳,可他们争的是做人的资格。”
话音未落,忽听宫外钟声大作??是鸣冤鼓!
连击三响,震彻九重宫阙。
侍卫飞奔来报:“启禀陛下,击鼓者非平民,而是……而是文枢殿七贤之一的沈经师!她带着三百弟子跪在宫门前,请求颁布《女子科举令》!”
皇帝神色不动,太子却怒极反笑:“荒唐!自古科举只为男子设,岂能因一妇人之言动摇国本?”
“国本?”皇帝冷笑,“若天下一半人皆无出身之路,那所谓的‘国本’,不过是半壁江山罢了。”
他拂袖而去,亲自迎出宫门。
雨又下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