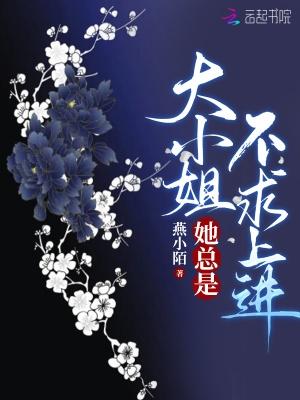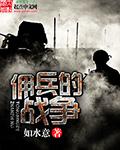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婴儿的我,获得大器晚成逆袭系统 > 第571章 第二轮比试(第3页)
第571章 第二轮比试(第3页)
他望向远方的山峦,轻声道:“我在等一个人。”
“等谁?”
“等下一个不敢说话的孩子。”
顿了顿,他又补充,“也是等下一个不敢听的人。”
二十年后,全球已有超过八万座行响学校,遍布城市与乡村。它们没有统一教材,没有标准化考核,唯一的共同点是:教室中央永远放着一只铜铃。任何学生,任何时候,都可以摇响它,要求全场安静,然后说出心里藏了很久的话。
而那只最初的铜铃,早已不再需要人为摇动。它悬挂在灯塔岛最高处,随风轻颤,叮咚作响。气象学家无法解释为何这座岛常年有风,哪怕在无风的日子里,铃声依旧清晰可闻。
有人说,那是大海在呼吸。
有人说,是地球在回应。
只有苏晚知道,每当有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鼓起勇气说出真话,那铃就会轻轻一震??像是心跳,又像是承诺。
她老了,头发全白,走路需要拐杖。孩子也已中年,面容平静如深潭。母子俩常并肩坐在海边,看日升月落。
“后悔吗?”有一天她问,“如果不是这个系统,你可以做个普通人,结婚,生子,过平凡日子。”
他笑了笑:“我就是普通人。我只是多听了一些故事。”
她望着他,忽然觉得,这双眼睛从出生起就没变过??清澈,专注,带着一种近乎神性的耐心。不是神明俯视众生,而是人与人之间最原始的凝视:我相信你,所以我在这里。
最后一场大规模集体坦白发生在她去世前三个月。
那天,全世界有超过两亿人同时登录公共记忆平台,上传一段音频或视频,标题统一为:“致未来的听众”。
苏晚录下自己的声音:“我曾经拍下矿难文件,以为能改变什么。结果亲人被害,朋友疏远,我躲进孤岛十几年。我很怕,很痛,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知道,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孩子愿意听我说话。”
发布后十分钟,平台上跳出一条匿名回复,只有五个字:
>“妈妈,我听见了。”
她笑着哭了。
葬礼那天,没有哀乐,没有悼词。全岛居民围坐成环,每人讲述一件与她有关的真实往事。有人说起她曾深夜冒雨送药给生病的孩子;有人坦白自己曾偷窃她的物资,事后羞愧难当;还有人哽咽着承认:“我当初反对你留下孩子,怕他会带来灾难。可现在我才懂,灾难从来不在他,而在我们不敢面对自己。”
太阳落山时,孩子独自走向海边,将母亲的骨灰轻轻洒入浪中。风很大,卷着细沙与咸雾。他闭上眼,仿佛又听见那个稚嫩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你们听见了吗?”
这一次,他回答了:“听见了。我们都听见了。”
海面平静下来,心语石缓缓升起,悬浮于水面之上,通体透明,宛如一颗跳动的心脏。它不再发光,却能让每一个靠近的人,清晰听见自己内心最深处的声音。
多年以后,当新一代的孩子们在学校学到这段历史时,老师不会说“英雄拯救了世界”,而是告诉他们:
“世界没有被拯救。它只是终于学会了倾听。”
而在太平洋某个无人知晓的小岛上,一位白发老人抱着新生儿,轻轻哼唱那首传遍海岸的歌谣:
>“你说出口的,就不会真正死去。
>只要还有人听着,
>回响,就永远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