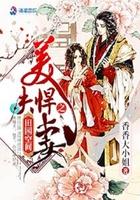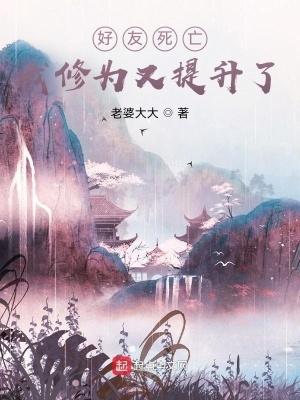铅笔小说网>[综武侠]肝露谷,但快意江湖 > 21741一更(第3页)
21741一更(第3页)
她还看见自己老了,白发苍苍,坐在一口早已熄火的锅前,手指抚过冰冷的陶片,喃喃道:“锅凉了……没人回来了……”
最后,她听见一个声音,来自四面八方,却又似从她心底升起:
“你真的以为,一碗汤能对抗整个时代的麻木吗?”
她猛然睁眼,跪倒在泥水中,大口喘息。
闪电照亮她的脸,泪水混着雨水滑落。
但她笑了。
“一碗不够。”她对着风雨嘶吼,“那就千碗万碗!一人不愿醒,那就百人千人万人拉他起来!你说时代麻木?我就偏要在这冰原上,烧出一口永不熄灭的锅!!”
翌日清晨,她召集所有人。
“我们要办一所学堂。”她说,“不教武功,不授权谋,只教一样??如何记住。”
陆昭皱眉:“现在风声紧,各大书院都在通缉‘记忆传播者’,办学风险太大。”
“正因如此,才更要办。”苏挽晴目光灼灼,“以前我们救人,是从火场抢人。现在我们要在火还没烧起来的地方,挖沟筑坝。”
于是,“忆庐”就此成立。
第一课,苏挽晴站在讲台上,面前坐着二十多个孩子,年龄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她没讲课,只端出一碗热汤。
“谁想喝?”她问。
所有孩子举手。
“好。”她点头,“但喝之前,我要你们做一件事??回家问父母一个问题:你们最后一次哭,是因为什么?”
教室安静下来。
傍晚,陆续有家长怒气冲冲找上门来,指责苏挽晴“蛊惑孩童”、“挑起情绪波动”。她不开门,只让小满从窗缝递出一碗汤。
奇迹般地,那些暴怒的父母喝下汤后,往往站在院外愣许久,然后默默转身离去,有的甚至蹲在地上嚎啕大哭。
三天后,忆庐门口排起了长队。
人们不再是为了孩子报名,而是为自己??他们想找回那个被药水抹去的拥抱,想记起某个人临终前握着他们的手说了什么。
苏挽晴依旧严格筛选,每人必须通过三问:
一、你是否愿意承受记忆带来的痛?
二、你能否保证,即使后悔,也不会回头举报他人?
三、你有没有一个无论如何都想再见一面的人?
只有答“是”的人,才能入门。
某日,一位老妇颤巍巍前来,耳聋眼花,拄着拐杖。她说是来找儿子的,可记不清名字,只记得他爱吃她做的酸笋面。
苏挽晴让她坐下,递上汤。
老妇喝下,忽然浑身剧震,双手猛拍桌子:“阿稷!你是阿稷!你说要去京城考功名,走那天我没给你多塞两个饼,我一直后悔啊!!”
她放声大哭,泪如泉涌。
苏挽晴轻轻拍她后背:“您儿子没考上。他在路上被人骗了盘缠,后来在一家客栈当杂役,去年冬天冻死在柴房。临死前,他嘴里一直念着‘娘做的面真香’。”
老妇止住哭,怔怔看了她半晌,忽然笑了:“那就够了。我记得他,他也记得我。这就够了。”